简介:恐怖 悬疑
《老贺的诡事辑录:一个退役军人亲身经历的恐怖记录》是一部以退役军人杨贺的亲身经历为主线的恐怖悬疑小说。1982年,主人公杨贺在部队服役,期间犯下错误,回家后遭遇一系列诡异事件,本不信命的他开始相信一个批命老人的话,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因此卷入了一桩天大的阴谋之中。一件件离奇诡异的事情连续发生,一个个心怀鬼胎的人连续出现。深山中隐藏的龙脉,紫玉金蟾牵扯出的秘密……种种诡异事件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阴谋?
前 言
一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他自称老贺。沏清茶一壶,备瓜果两碟,他是讲故事的人,我是听故事的人。他的故事惊悚离奇,荒诞怪异。由于他的叙述简洁凌乱,所以我就将我听到的故事作了文字加工,为了叙述方便,我在故事里用了第一人称,就是你们下面即将看到的。
第一章 红棺女尸
1982年,我在东北的某高炮团当一名炮手,那时候我们驻扎的地方比较荒僻,所以除了每天基本的训练,日子过得很无聊。
六月二十五号那天,天阴沉沉的,我换完岗后疲倦地倒在床上睡觉,睡得正香的时候被人一把推醒了:“嘿,杨贺,贺子,快醒醒,有个新鲜事儿告诉你!”
我睡眼惺忪地一看,原来是柳松明,外号柳黑子,班里就数他和我的关系最铁。
“去去,有什么新鲜事儿?没看我这睡得正香呢。”我没好气地给了他一拳,睡觉时被人弄醒,恐怕没人会高兴。
“真的,我没骗你,刚才巡逻下来后,我听他们说在营地北面三四里的地方看到了一口红色大棺材,一半埋在土里,红色的,凶啊。”
“瞧你个没文化的,那叫朱漆棺材。有人打开看了吗?”我看他是打定主意不想让我继续睡,索性就坐了起来。
“嘿,你还别说,三班的高大炮还真是胆大包天,本来没人敢过去,偏他就没当事似的把棺材盖儿给掀了,说是里面放着一具女尸,而且眼睛和鼻子上还缝着红线……”
“又是他。”我小声嘀咕。
高大炮原名高大强,整个团里,就属我和他不对付,我们一个号称浑身是胆,另一个自称胆大包天,自古“文无第一,胆无第二”,我们是谁也不服谁,总想争出个高低来,可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我听着柳黑子一直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地说着那个女尸的事儿,突然心中一动,想起以前大人经常给小孩讲的打赌喂死人吃饭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让高大炮吃瘪的主意。
我拽了他一下:“黑子,你去帮我给高大炮传个话。”
“什么话?”柳黑子不明所以地看着我。“你就说我要找他打赌。”
“打赌?”
“你告诉他今天晚上十二点,让他拿着一碗饭去喂那个棺材里的女尸吃,不许拿手电之类的照明。如果他做到了,以后我杨贺就服他,事后还请他喝酒。”
柳黑子一脸诧异地看着我:“我说你……别闹了,人都死了还怎么吃饭?”
“那你就别管了,叫你去你就去。”我想自己的点子肯定能挫挫高大炮的锐气,心里别提多兴奋了。
黑子最后还是替我传了话,没想到高大炮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大概他也早就想挫挫我的锐气了。
我要和三班高大炮打赌的事一来二去地传了出去,我们那时候比较松散。到了晚上十点多的时候,虽然天上下着小雨,但在营地门口还是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大家都议论纷纷,高大炮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心中暗自冷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一会儿就有你好看。
快十一点的时候我捂着肚子满脸痛苦地对黑子说:“黑子,我突然肚子疼,先去方便一下,你帮我在这看着啊。”
“行,你快去吧。”
我捂着肚子在营地门口拐了个弯,跑向了黑暗处。那边高大炮穿着雨衣手里还端着一碗饭,向着放朱漆棺材的地方出发。其实肚子疼是我装的,早在下午的时候我就按照黑子的描述找到放朱漆棺材的地方了。
那地方地势有点儿古怪,方圆半里都没有树木,只有及膝的荒草。放置朱漆棺材的地方是个凸起的土包,朱漆棺材入土一半,棺材上的朱漆艳红如新,很是诡异。
对于这个突然出现来历不明的棺材我谈不上惧怕,顶多是有些不舒服,但是为了打赌也就顾不上这些了。
下午来的时候我看好了一条小道,虽然难走些,但是就凭我的脚力应该会比高大炮早到。
我沿着小路拼命地跑,因为速度过快,手电筒几次差点儿脱手而出。我一面死命地攥住手电筒,一面调整自己的呼吸。
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一会儿没看到树木了,似乎已经到了地方,可是周围黑糊糊一片很难辨认,我拿着手电筒四处一照,果然,北面有个红色的东西一闪,正是那口朱漆棺材。
看到棺材,我心中一喜,看来我果真比高大炮早到一步。
我将手电叼在嘴里,上前费力地把棺材盖儿掀了起来,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透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屏住了呼吸。
手电筒幽绿的光照到了棺材里躺着的女尸脸上,我清楚地看到,在女尸的眼睛和鼻子上缝着几道红线。
女尸的脸上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惨白,我怕高大炮随时会来,也顾不得害怕,俯身就将女尸抱了起来。女尸的身体僵硬如铁,透着一股瘆人的冰冷,我一咬牙,走到土包的旁边寻了一处草长得高的地方将女尸藏好。
这时候不远处隐隐传来脚步声,我知道肯定是高大炮来了,急忙翻身躺进了棺材,然后从里面把棺材盖儿推上。
棺材盖儿一合,世界马上寂静下来。我躺在棺材里,手指无意中摸了一下身下,凉凉的,下面似乎垫了什么东西,躺起来并不觉得硌人。
我来不及感受更多,头上的棺材盖猛地被人给推开了,是高大炮来了!
躺进棺材的时候,我已经把头上的雨衣帽摘了下去,还把一堆黑色毛线扣在了头上,黑糊糊一片,我就不相信高大炮能看清我的脸。
我死死地闭着眼睛,屏住呼吸,就听高大炮在头上念叨:“这位大嫂,我知道你都死了我还来打扰你实在是不好。不过我和一个战友打赌,不得不来,你就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千万别出来吓我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听到高大炮嘴里碎碎念,心中好笑,原来这也是个外强中干的货色。
高大炮念了一会儿“阿弥陀佛”又说道:“我这有一碗饭,我就放在你嘴边,省得杨贺那小子以后抵赖说我没来过。”
说着高大炮就从雨衣兜里掏出个勺子,又从碗里挖了好大一勺饭送到我的嘴边。
我眯眼一看,心想:好小子,好戏就要开锣啦!等到那口凉透了的饭送到我嘴边,我猛然张大了嘴,一口连勺子带饭全都咬到了嘴里。
高大炮感觉手上的勺子被咬住了,顿时浑身一抖:“你……”
我嘴一松,勺子抽了出去,我故意用很大的声音咀嚼着嘴里的饭,那吧唧吧唧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分外瘆人。
我听到高大炮牙齿打战的声音,心中暗笑,看你以后还有脸在我面前自称浑身是胆!
嚼了一会儿,那口凉饭终于被我咽了进去,高大炮胆子还真不小,我刚把嘴里的饭咽下去,他竟然又颤颤巍巍地递过来一勺,我照旧把饭大嚼一通再咽下去。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高大炮带来的饭全都被我吃进了肚。
我心中懊恼,没想到高大炮竟然没跑,饭全都喂完了,难道说这次打赌我输了?我有心出声吓他一下,但是又怕他听出我的声音,到时候面子上不好看。
这时候高大炮说道:“这位大嫂,现在饭你也吃了,我要走了。我们只是萍水相逢,你千万别来找我啊……”
我眼看着他将棺材盖儿合上,心中直叹气。突然高大炮惨叫起来:“别拉我,别拉我,求求你……”外面传来剧烈的撕扯声,棺材盖儿都挪了位。
我透过缝隙看到高大炮两手拉着雨衣的下摆,满目骇然,仿佛有人拉住了他的衣服。
我不明所以,心中也不禁害怕起来,难道真的有鬼?
高大炮剧烈挣扎了几下,突然快速地解开了雨衣的扣子,惨叫着消失在雨中。
我抹了一把脸,把棺材盖儿一把推开,跳了出去。扭开手电筒,光线打在棺材盖儿上,我仔细一看,高大炮的雨衣在微风中飘着,一边却夹在了棺材和棺材盖儿之间。
我急忙跑到藏女尸的地方一看,女尸还好好地躺在那儿,细雨蒙蒙里更显得可怖。
我顿时松了口气,哑然失笑。肯定是高大炮打开棺材的时候棺材盖儿夹住了他的雨衣,他惊慌之下就以为是棺材里的女尸想要留下他,所以才会怕成那样吧。
我将湿漉漉的女尸抱起来重新放进棺材,谨慎地合上棺材盖儿,至于高大炮的雨衣我也没去管它,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赶在高大炮前面回到营地。
我还是从来时的小路原路返回,心中急切,脚下的步子就迈得特别大,一个不慎手中的手电筒竟然摔了出去,我也顾不上了,跟着感觉走吧,还好不一会儿就看到了营地门口的灯光。
我远远地就看到营门口依然聚集着很多人,大家都在翘首观望,看来高大炮还没回来。
我悄悄地顺着围墙爬了进去,然后在墙角把身上的雨衣整理了一番,然后装作不经意地走到了柳黑子的旁边。
柳黑子看到我问道:“你拉屎掉进坑去啦,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我捂着肚子“哎哟”了一声:“谁知道今晚吃什么不对劲儿了,肚子难受得要命,蹲得我脚都麻了。那什么,高大炮还没回来吗?”
“没回来,不会真的遇到鬼了吧?”柳黑子的表情有些发毛。
我故作生气地说:“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些迷信思想。”
柳黑子捂着嘴连连点头,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了,但是在部队里说起这些唯心调调,要是被领导听见会认为这个战士的思想不够成熟,会影响复员以后的分配。
这时候站在前排的人突然一阵喧哗:“看,看,回来了!”
我挤到前面一看,果然高大炮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到了近处,就看到他面色惨白,身上没穿雨衣,脚上少了一只鞋,浑身湿漉漉的,狼狈不堪。
一伙人急忙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问他到底喂没喂女尸吃饭。
高大炮哆嗦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喂了。”
大伙看他的样子有些不对劲儿,雨衣也没了,追问得更起劲儿了。
高大炮白着脸半天没说话,我走到他身前,他才道:“杨贺,我喂的饭女尸全给吃了,我没撒谎,你信不信?”
我看到他的样子心里颇有些后悔,好像玩得有些过分了。我毫不迟疑地点点头,不管怎么说,我的要求他的确做到了:“高大炮,这次打赌你赢了,我服你!”
高大炮嘴边泛起一抹苦笑,全无得意之情,然后就像个游魂似的走进了军营。
大家在他后面惊疑不定地小声议论着,都说高大炮是不是吓糊涂了,女尸怎么能吃饭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听说高大炮病了,好像病得还不轻,也不知道是因为淋了雨还是被吓的。总之发高烧说胡话,被折腾得够戗。
说实话我真的后悔了,但是又实在没勇气对他说出真相。
我被班长叫去给狠批了一顿,之后我去看高大炮,他已经被转到附近的部队医院去了。这里的部队医院条件并不太好,简单的病床上,高大炮满脸通红地躺着。
我轻轻把带来的一袋饼干和几斤苹果放在了他的床头,他手上挂着吊瓶,眉头紧紧地蹙着,仿佛正陷入噩梦当中。
我刚要走,就听见他用极度惊恐的声音说道:“别拉我,别……求求你,放过我……放了我……”我的心被紧紧地揪了起来,嘴里有些泛苦。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高大炮,听说他病好以后,通过申请被调到别的军区去了。
至于那口莫名出现的朱漆棺材,事后我去看过,已经不见了,只在放棺材的小土包上留下了高大炮的雨衣。
自那以后,我经常会做噩梦,后来我才明白,那只是我一切厄运的开始。
八月二十三号,我犯了一个极为重大的错误,是什么错误我不想再说,只是那次犯的错足以让我蹲上三到五年。因为我父亲在市里有些影响力,也因为我是初次犯错而且认错态度良好,所以最后只开除了我的军职,让我复员回家。
我满怀痛苦地走了,走那天好几个战友来送我,那场面任你是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住。我拉着柳黑子和班长的手哭得一脸的眼泪鼻涕。
“回去后好好地端正态度,好好地做人……干什么都不能堕了咱军人的身份……”班长拉着我的手殷切地嘱咐。
我哭着点点头,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军营。
走出军营,还要走十几里的土路才能到车站,我拎着行李浑浑噩噩地往前走,八月的太阳烤得人心慌。走了四五里路的时候出现了一条岔路,那条岔路是一条小道,是通往一个小屯子的,我每次回家探亲的时候都会路过这里。这时候我看到小路上有一辆驴车被一个深坑卡住了,一个身穿坎肩的花白胡子老大爷,正吆喝着毛驴往外拉。
我连忙放下行李上前帮忙推车,我们费了好一番工夫才把驴车弄了出来。
老大爷笑着对我道谢,又道:“小伙子,要回家吧,要不要上来我送你一段?”
我正好走得有些累了,就满怀感激地应了一声,跳上了驴车。
车上,老大爷叼起了烟袋,上下打量了我几眼:“小伙子面相不错啊,可惜破了。”
我听到他这话说得奇怪,就问道:“大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伙子是不是最近诸事不顺?”
“是……是啊,你怎么看出来的?”我有些吃惊地看着他。
老大爷呵呵一笑:“以前学过一些,为这个没少挨斗,还好熬过来了,还是现在的日子好啊。”
我知道他的意思,这老大爷以前肯定是学过一些相人相面之类的本事,“文革”时就是要打倒这些封建思想、牛鬼蛇神,所以他说现在熬过来了。
“大爷你会看相啊。”
“雕虫小技而已。”
老大爷说完这句话就眯着眼开始抽烟,那旱烟味儿极是呛人,差点儿把我的眼泪熏出来。过了一会儿我沉不住气了:“大爷,我最近干什么都不顺,你能看出是为什么吗?”
老大爷嘿嘿一笑,往车板上磕了磕烟袋:“本来老头儿我也不想说,但是看在你我同车有缘,我就随便说两句吧。
“小伙子,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
我随口就报上我的出生日期,老大爷用手指掐算了几下,赞叹着点头:“好生辰哪,天上三奇甲戊庚,地下三奇乙丙丁,人中三奇壬癸辛。你这是三奇贵人的命格,列吉星次首!”
我听着糊涂,但也大致明白我的命格应该是极好的:“大爷,你的意思是我的命应该是挺好的吧,但是我最近为什么……”
“小伙子,你的命格确实极好,但是此类命格也大有缺陷,如遇咸池、元辰、冲破等就不灵验。”
“什……什么意思?”
“嗯,这么解释吧,小伙子你听过咸池吗?”
“哦……”我的脸涨得通红,“有点儿耳熟……”
“咸池是日入之地,传说西方王母娘娘拥有很多年轻貌美的侍女,而咸池是专供她们洗澡的地方。天上的仙女自然是美丽的,古人形容美女多用面若桃花,所以这个咸池又叫桃花池。咸池就是桃花的意思,亦指女色。而元辰就是指毛头星,是凶星,元辰入命诸事不顺,如果是男性,最怕情事桃花或是酒色之灾。”
我的脸红了又红:“是女人洗澡的地方啊……”
老大爷古怪地瞥了我一眼:“你前段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情事纠纷?或是碰过比较特别的女人?”
我摇摇头:“我一直在部队里待着,哪有机会接触女人?情事纠纷就更别提了。”
我挠了挠头:“我长这么大还没谈过朋友,家里说我复员以后要给我介绍个女同志,不过还没见过面,不知道算不算?”
老大爷吧嗒了一口旱烟:“那不算,必须有身体接触的才算。”
我突然一个激灵,想起了和高大炮打赌的事,结结巴巴地道:“死人……死人算不算?”
老大爷的眼光突然定在我脸上不动了:“你是说,你接触过女尸?”
“是啊,就在两个多月前。”我已无意再隐瞒那件事,就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这也是你命里该遭的劫数。依你所说,你遇到的女尸六月冰寒,眼鼻处缝红线,棺木入土一半,半里内无遮阴之木,这是因为那个女人死得凶啊。
“按你的命格,二十五岁之前不宜近女色,也不宜太近接触死人和凶地,你咸池、冲破两项齐遇,哪还有不倒霉的道理?”
“可是……可是那是具女尸,算不上什么女色吧……”“你可能不知道,身犯败神桃花煞的女人死的时候才会在眼鼻处缝红线,那女尸虽算不上女色,但是要比普通女色凶上十倍!”
我一听,整颗心顿时就像寒冬腊月的馍馍——透心儿凉了。我回想这段时间的遭遇,似乎真如老大爷所说,从和高大炮打赌开始就没平静过,难道那具女尸真的破了我命中的吉运?
我迷迷糊糊地想了一阵,突然清醒,不对啊,我是个解放军战士,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受的是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教导,怎么能相信这样的无稽之谈?
虽然我没打过越战,但是在部队里也磨炼了一两年,部队除了锻炼我们的体魄还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我不能因为一时的软弱就听信这些封建老八股。
我摇了摇头,又摇了摇头,老大爷本来还在说话,一见我的神情突然变了,顿时就住了嘴,叹了口气。
驴车上没了说话声,只有老大爷吧嗒吧嗒抽烟的声音。
又走了大约十分钟,我看到了建在土路边上的简陋车站,拎起行李就跳了下来。
“谢谢你,大爷,我到地方了。”
“嗯,”老大爷挥着鞭子“哦”了一声,“小伙子,你好自为之吧。要是实在挺不过就来找我老汉。”
鞭子一扬,老大爷赶着驴车走了,我站在原地琢磨他的话,觉着不对劲儿,他也没留下姓名和住址,就算我以后真要找他,也找不到啊。难道他还是得道高人不成,在我有难的时候说来就来了?
我为自己的想法哑然失笑。
坐在车站里等了半小时才来了一班客车,那时候的客车很少,一般每天就两趟,我急忙挤了上去。客车里人很多,跟煮饺子似的,动一下都困难。
好不容易到了市里,我下车的时候脖子都硬了。
我一路小跑向着自家的方向奔去,心里还是挺激动的,离上次回家都有好几个月了,说不想家那是骗人。
我家的住房去年刚换,我从小在筒子楼里长大,那段岁月真是不堪回首。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住在筒子楼里的时候,我们三个每天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就像是经历一场大战。我每天听着姐姐的呼噜声,闻着弟弟的臭脚味,有段时间都想离家出走……
我三两下蹿上了二楼,刚敲门门就开了,还没等我反应我妈就哭开了:“孩子啊,你要妈怎么说你呀……”我苦着脸等我妈数落完,才灰溜溜地进了家门。等待我的,又是我爸的一顿狠批。
我垂头丧气地站着,一脸凄苦。这时候我妈反倒心疼起我来,忙上前安慰了我几句,真是天下父母心,有的就只是一颗疼爱孩子的心。
为了慰劳我,我妈中午做了一锅猪肉炖粉条。看着桌子上热气腾腾的猪肉炖粉条,我突然想起了刚到部队那年,中秋节我回家的要求没有批准,我沮丧地待在宿舍里发呆,是班长自己掏了钱让食堂做了好大一锅猪肉炖粉条,我们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吃菜、吃月饼、过中秋,而现在……
我抱着菜盆子一时间眼泪就下来了,我爸刚伸出的筷子被我妈打了回去:“贺子,别哭了!你吃,这一盆子都是你的……”敢情我妈以为我是馋哭的。
第二章 西甩弯子村
在家赋闲了半个月,家里虽然热闹,但是我的心空空的,总有种很不安的感觉。
九月十号,这种不安终于被证实了。
那天上午,我妈还挺高兴地告诉我,复员的工作有着落了,就安排在我爸所在的厂子里,成为麻纺厂里的一名科员。
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我的不甘心,晚上的时候,我爸就没回来。
我妈连夜去打听,才知道我爸因为作风问题突然被上面隔离审查,具体原因也说不清,好像和在厂里搞派系有关。
“文革”时期,派系成风,什么东风派、红旗派之类的,“文革”结束后就对这个遗留问题比较敏感,稍有动静,就会严厉打击。
我妈担心得夜不能寐,我们姐弟几个如何安慰也没用。
又过去两天,我爸那头还是毫无动静。我妈在房间里走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她拉着我的手哭道:“贺子啊,你爸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你的事儿是你爸走了门路的,我怕这次再把你也整出来……妈想了一晚上,你走吧。”
“我走……”我脸上一片惶惑,“上哪儿去?”
“妈想好了,你下乡去躲躲,等你爸的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那时我已经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只有按照我妈的话去做了。
在我妈的安排下,我坐了一天的客车又转了一趟车,车走到半途,售票员喊了一句:“河西村到了,下车的赶快!”
我拎着沉重的行李跳下了车,我妈说的,只要到了这里就会有人来接我。
我站在路边来回张望,这里的环境和城市有着天壤之别,天又蓝又高,我仿佛都能听见河边的蛙鸣声。
在路边站了二十多分钟,我忽然看到有一辆牛车慢悠悠地向我走来,上面坐了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男人,头上还戴了顶露洞的草帽。
他看到我立刻停下了牛车,试探着说:“你是……杨贺?”
我高兴地点点头:“你一定是我表舅赵有强吧!”
没想到他竟然摇摇头,面上带着憨笑:“赵有强是俺爹,我是他儿子赵二柱,你叫我二柱就行了。”
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在近处仔细一看,他果然没那么老,可能平时干农活过于操劳,才弄得面相着急了些。
“快上车吧,”他说,“知道你要来,家里都准备好几天了。”
我跳上了牛车,二柱赶着牛车往回走。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奇怪地问:“还没到吗?”
“咱家不在河西村,得从这绕一段山路再过一条河才到。”
拉车的老黄牛韧性很强,我们一直走到日落西山才到了我表舅的住处——西甩弯子村。
我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和表舅一家寒暄了几句就坐上炕头大吃起来。
吃完饭,我拿出我妈给表舅一家准备的礼物。那是两件“的确良”衬衫,一个印有“上海”字样的黑色皮包和一罐茶叶。
别小看这几样东西,在当时的年代,那已经是相当重的礼,不亚于现在一套足金首饰。我果然看到表舅一家眼中放光,舅妈欣喜地抚摸着“的确良”衬衫,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真好,还是这料子摸着舒服……”
我妈送这么贵重的礼是有原因的,她不知道我爸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完,怕我在这儿受委屈……
表舅家的生活条件一般,“文革”后国家改变政策,农村实行单干,我表舅一家四口卖力干活,也只盖起了一间青砖打基础的土坯房。
表舅将我安排在房子边上一间很小的屋子里,不用跟他们一家挤在一张大炕上,着实让我松了口气。
我躺在晒过的棉被上,心中五味杂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呢?
睡了一宿觉,我随着表舅家的人早早就起床了。
吃饭的时候,我表舅的大儿子大柱突然满脸惊慌地跑了进来。
“大柱,怎么了?”
大柱脸色煞白:“爹,六婶又犯病了,六叔让你帮着请大神二神来。”表舅一听马上飞身下炕,跑了出去。
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大柱转身就跑了,二柱和舅妈撂下饭碗往外走,我也跟了上去。
六叔家和表舅家就隔着一个菜园子,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土坯房,立刻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只见简陋的土坯房里,一个浑身一丝不挂、瘦骨嶙峋的妇女正在炕上爬,腹背处有一道道的血痕,嘴里还发出一种类似野兽的嘶叫声,披头散发的,让人看不清她的脸。
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正死命地按着她,憔悴的脸上涕泪交重。
二柱和舅妈马上就扑上前,帮男人抱住正在爬的女人,没想到那女人一个挺身,竟将三个人都甩在了一旁。
接着就发生了让我到死都忘不了的一幕,那个女人竟然头下脚上,顺着贴满报纸的土墙爬了上去!
我们都惊叫了起来,女人迅速地爬到了屋顶,那姿势分明像一条蛇。二柱首先反应过来,叫道:“六叔,一会儿六婶醒神儿可就糟了,我们得想办法把她弄下来!”
我们几个合力抬来了一张破桌子,六叔和二柱上去就要把六婶扯下来。
这时候传来一阵铃铛声,屋里进来了一男一女。我转头一看,这两人身上穿着蓝色劳动布衣服,上身缠着几道红布,腰上还绑着一圈铃铛,女的手里拿着一根缠着彩布的一米多长的杆子。
表舅也随后进来了,不大的小屋立时被塞得满满的。
那两个跳大神的看到六婶在屋顶上倒吊着竟然毫不惊慌,女大神爬上了炕,一抖手上的杆子就开始唱。
我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场面,眼睛都不够看。女大神唱的腔调很怪,我模模糊糊地只听懂几句,好像是“扬鞭打鼓请神仙……哪吒闹海精钢圈……仙童哟……你来了……不要吵也不要闹……”
那个男二神就配合着她一起跳,两人在炕上一阵闹腾。说也奇怪,他们唱起来以后,六婶就不再爬动了,一直吊在那儿,头部来回地转动。突然“哎呀”一声,手脚像失了吸力似的,一下子掉了下来。
还好六叔和二柱一直站在她下面,马上就接住了她,这要是直接掉在地上,肯定得摔个好歹。
把人放到炕上后,舅妈马上帮六婶把衣服穿上了。六婶像失了心魂似的坐在土炕上,两个跳大神的围着她又唱又跳。
突然,六婶把脖子高高地仰起,用手在屋里一干人的身上来回地指,然后就停在我身上不动了。
我蒙了,就听见六婶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不信,你给我磕头!”
晴天霹雳!
我刚想溜,那个女大神开口了:“她是蛇仙上身,不照她的话去做,有人会死!”
我当然不要!我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怎么能因为迷信给人磕头?
我倔犟地站在那儿,嘴角抿得死死的。眼看六婶又开始浑身发癫,六叔含着泪就要给我下跪,表舅一家也恳切地看着我。
我眼一闭,牙一咬,就当过年给爸妈磕头了!
我跪下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头,然后转身跑了出去。
我站在屋子外面,心里这个气,这算什么?我到底跑到什么地方来了?
屋里跳大神的声音停了,表舅一家走了出来,看我负气站在那儿,二柱过来将我拽回了家。
二柱显然不善言辞,满脸的歉意却不知说什么话安慰我。我最后憋不住问他:“那个六婶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她真是什么蛇仙上身吗?”
二柱叹了口气,拉我坐在表舅家门口,和我说起了这件事。
六叔本名张存善,他媳妇叫翠花。他们两口子本来挺好的,两个女儿都嫁到了邻村,还有一个儿子才二十岁。六叔能干,六婶贤惠,日子过得还不错。
就在两个多月前,六叔的儿子上山拉柴火,不知怎么就死在山里,六叔六婶赶到山里,当时那个惨哪,就甭提了。回来后六婶就得了这个病,没几天就折腾得骨瘦如柴。
大伙一合计,用牛车把六婶拉到了城里的大医院。当时医院诊断六婶得的是癔症,可是汤药针剂都用上了却一点儿也没见效。后来只好把六婶又拉了回来。
回到家里,六婶隔三差五地就要犯上一次病,六叔病急乱投医,只好请了跳大神的来,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转眼被掏空了一大半。
可气的是,六婶依然犯病如故,一个家眼看就要垮了,表舅一家和六叔家关系很好,也跟着着急。
至于是不是蛇仙上身,二柱对于这个问题很迷茫,要说不是吧,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赤手空拳地在墙上乱爬,就算是特种部队也做不到啊;要说是吧,又觉得这种事太玄了,总之是谁也弄不明白。
我听了二柱的叙述也很迷惘,这世上解释不明白的事太多,我们自以为是万物之灵,是不是太浅薄了呢?
我在表舅家住了很长时间,后来又见过几次六婶发病,不过她并不是每次都会爬到墙上去。
一个多月后,六婶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眼看就不行了,他们家从城里来了个亲戚,不由分说就把六婶带走了,不过不是带到城里,而是带到了别的村子。那地方有一个著名的老中医,给六婶看过之后连开了三十六服汤药,六婶换了环境又吃了药,病情渐渐有所好转,在那儿住了半年多才回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促进文化交流,本站整理收录的小说资源均源自网络公开信息,并遵循以下原则:
1、公益共享:本站为非盈利性文学索引平台,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收费性质的阅读与下载服务;
2、版权归属:所有作品著作权及衍生权利均归属原作者/版权方,本站不主张任何内容所有权;
3、侵权响应:如权利人认为本站展示内容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把该作品相关材料私信至站主或者发件到邮箱。经过核实后,本站将会在48小时内永久下架相关作品。邮箱tegw202@gmail.com
4、用户义务: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利用本站资源进行商业牟利、盗版传播等违法行为。
5、我们始终尊重原创精神,倡导用户通过正版渠道支持创作者。如对版权声明存疑,请联系我们进一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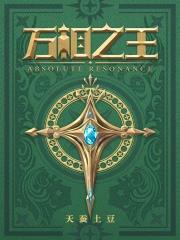


![《[最新]豪乳老师刘艳》连载 (1-9部35章+番外同人) 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uploads/2025/03/20250408195915145-《豪乳老师刘艳》1-8部120章-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jpg)















![表情[xiaoku]-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xiaoku.gif) 三十多兆的小说。。。
三十多兆的小说。。。![表情[tuosai]-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tuosai.gif)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