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武侠
胤匡武帝圣王七年十月十五,雨。
天罗刺客们撑着伞,进入了大胤的都城,拉开了猩红的大幕。
六把刀,一个守望者,七个人,一场刺杀。
苏小钏,边大,边二,舒夜,龙泽,安乐,荆六离。
秘密暗行,内鬼潜伏,最锋利的刀一一于天启城中折戟沉沙。
在星辰与月的黑幡旗下,天罗对弈辰月,天地一局棋。
牺牲与荣耀,背叛与深情,皆是手中棋、身后花。
所有的波谲云诡,都融进了天启城上的淡淡薄暮。
【CHAPTER1 历史背景】
大胤立国两百三十年后,葵花吸食着年轻人的血盛开在天启城外的荒野中。
胤匡武帝的继位是整个故事的序章。
胤匡武帝白崇吉,大胤开国皇帝白胤的第九代孙。这个原本绝无机会继位的年轻人获得了上天的青睐,超越尘俗的隐秘宗教“辰月教”的大教宗古伦俄把青眼抛给了白崇吉。于是白崇吉在群狼围伺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继承了空悬一年零三个月之久的大胤王朝帝位,宦官当政的“无王之治”就此彻底结束。
白崇吉继位的当天,古伦俄踏入天启城。这位秘密宗教的执掌者选择了从神坛上走下,足履人世间的尘土。
十二匹白得胜雪的攸马拉着长车,它们的长鬃洁白胜雪,飘洒着像是丝绸,独角上闪着水晶般的微光。天启城门口围观的人们交口称赞这架马车的华贵,猜测车中主人的身份,而古伦俄却没有掀起漆黑的绣着星辰和银月的车帘。这位高贵的羽人并非为了爱与平安而来,当时围观的人还不明白这一点。
次日,古伦俄被奉为国师,十二个月后,辰月教被尊为国教。成百上千黑衣的教众从四方向着帝都天启汇聚,他们高举着辰月的黑幡,面前低垂着飘摇的兜帽,以绝对的沉默经过大街小巷,最后无一例外地去向了“天墟”。
这是皇帝为古伦俄新起的神宫,宫门永远敞开,可是没有人敢于走进去。越过围墙可以看见这座神宫用巨大的石块堆垒而成,不是东陆人所熟悉的建筑风格,雄伟的中央祭坛刺向天空,像是平地拔起的小山。
随后“天墟”的“教旨”俨然以高于圣旨的威严和数量向着全国各地颁布。诸侯们意识到帝都的变化时,已经太迟了,经过短暂的对抗之后,楚卫、淳、唐这三大强国本着对于皇室的忠诚接受了大教宗的教旨,君主们率先宣布接受辰月的教义。而剩下的诸侯国也只有一一归附。
诸侯们的退让换来了六年的表面平静,可战火却没有一刻停息。
六年中,诸侯间发生了大量的冲突,率先归附辰月的三大强国获得了大教宗的恩宠,其余诸国稍有违逆,立刻有教旨命令附近的大诸侯起兵征讨。通常直到强国兵临小国都城之下,小国国主呈来痛不欲生的悔过奏折,大教宗才会下旨休战,而已经被夺取的城池、人口和资货都归于勤王的强国所有。三大强国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就在人们以为东陆诸侯国的格局将演化为三大诸侯国时,北陆传来惊人的消息,一直处于频繁的内战中的蛮族诸部中出现了一位绝世英雄。逊王阿堪提,这个甚至没有姓氏的奴隶崽子骑着他的骏马,带着他仅仅七千人的子弟逼迫蛮族所有部落坐下来一起说话,蛮族诸部在阿堪提的战刀下一起跪倒,表示尊奉共同的祖先盘鞑天神,从此诸部落世代为兄弟。
阿堪提整顿了自己的后方后,立刻带着轻骑兵南渡,海潮流向的变化使得天拓海峡这个天堑变得水流平缓,阿堪提甚至获得了羽人提供的木兰长船,有人传闻掌握了羽族命运的大祭司古风尘和阿堪提是亲如兄弟的敌人。
东陆人面对骑在矮马背上的蛮族轻骑兵,陷入了绝望。这些生活在马背上的人可以数十日不下马地征战,他们的马不挑草料,随处可以获得补给,而他们自己用弓箭狩猎获得食物,根本不需要辎重跟随。他们也不攻城略地,他们迅速地绕过城市直击富饶的村镇,夺走他们的粮食和器物,杀死全部的男人,凌辱无助的女子。
最后,一个孤身突进的蛮族轻骑出现在天启城墙下,这个一辈子生活在茫茫大草原上的蛮子呆呆地看着面前雄伟的都城,惊讶得合不拢嘴。而城墙上的大胤士兵也傻了,大胤的历史还上从未有蛮族人杀到帝都的事发生过。大教宗古伦俄沉默地走出了天墟,登上城墙。他遥遥地和那个蛮子对视了一会儿之后,从黑袍下伸出苍白的手,接过教徒递来的黄杨木弩,准确地射死了那个蛮子。
这是大胤王朝对于蛮族的正式宣战。
唐国和楚卫国迅速接到教旨,集合了最强的兵力越过殇阳关的屏障,直扑北方,在中州高原上与奋勇抵抗蛮人半年之久的淳国铁骑兵汇合,三国强兵试图一举歼灭入犯的蛮族轻骑。可谁也没有预料到,就在决战的前夜,蛮族轻骑准确地摸索到了设在长炀川隐秘处的中军主帐,一举歼灭了包括楚国公白麓山和淳国公敖休在内的精英将领,唯有没有入睡的唐国公百里冀以自己两个儿子的牺牲为代价,逃脱了青阳部鬼弓的长箭。
百里冀是隐忍而英伟的人物,清楚在这种时候不宜再图谋进攻。此时的淳国境内只有都城毕止凭借着高大的城墙尚能却敌,小城池里人人都是惊弓之鸟,神出鬼没的蛮子拉着角弓躲在城外暗处,射杀敢于踏出城门的人。百里冀决定引兵退出淳国国界,向着天启城进发,在帝都城下守住东陆的心脏。
而百里冀又一次没有想到,此时此刻所有的蛮族精兵都接到了命令,正悄悄地从四面八方向他逼近,一张围捕他的网已经张开。就在百里冀的奏折送到皇帝座前,请求背靠天启城墙陈兵防御的时候,蛮族人的进攻开始了。措手不及的百里冀陷入了苦战,请求天启开城,放入溃败的三国军士。
古伦俄再次出现在城头,依旧接过了教徒递上的黄杨木弩,连续三箭射在百里冀面前,断了他的退路。天启城的城门死锁不开,而忠勇将士的鲜血渐渐地漫过了百里冀的脚面。这个忠诚的诸侯和悲愤的英雄终于明白他和他所征讨的那些小国一样,不过是大教宗手中的棋子,一个棋子吃掉另外一个,而第一个棋子终究也不免被牺牲掉。
他不能救他的将士,也不能守卫他的帝都,于是愤怒地指天发誓,百里氏的子孙即使只剩最后一人,即使手里只有最后一枚钉子,也要钉在古伦俄的喉咙里杀死他。然后百里冀横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他的尸体在战场上站了一天一夜之久,最后蛮族的马队里走出了小个子的男人,轻轻一手推倒了他。有人说那便是逊王。
奇怪的是,蛮族人并未趁胜攻城,他们悄无声息地退去了。
传闻这根本是一场交易,古伦俄以东陆精英军队的战死,换来了逊王的退却,也换得了辰月教的绝对权力。
这时的九州像是一局诡异的棋,对弈的是古伦俄、古风尘和逊王三人,然而对弈的人,死得却并不比他的棋子慢。半年之后,逊王死在了北陆,死在了蛮族人自己的刀下。而羽族大祭司古风尘也奇怪地失去了踪影。
仅剩的是大教宗古伦俄。他的教旨和忠于他的徒众依旧横行在东陆的土地上,失去君主的三大诸侯国同时迎来了天墟的使者。继承人已经被大教宗选好了,三国没有选择,三个傀儡被扶了起来,雄才伟略的贵族子弟被软禁起来。楚卫白氏、唐国百里氏、淳国敖氏,这些尊贵的家族甚至连自己的部队都不能轻易调动了,复仇成为奢望。
而后出现的人没有让百里冀失望,他最小的儿子百里恬,这个孱弱的年轻人在宗族的大会上站了起来。他说我的父亲说,即使最后一个百里氏的子孙拿着一根钉子,也要把古伦俄钉死在天启的城墙上,我们没有了战刀,可是我们可以求助于阴影里的钉子!
随后的史实是模糊的,但是所有人都相信百里恬抛下贵族的尊严求助于东陆最可怖的影子组织“天罗山堂”。这个豢养了最优秀的杀手、存在于阴影里的权力组织对百里恬表示了认可,于是近百名优秀的天罗杀手潜入帝都,几个月之间帝都变成了屠场,无数天墟的高位教徒被杀死在黑夜里。
杀手,这是百里恬唯一能找到的钉子。尽管只有一点点锋刃,但是配合着百里冀死前的怨毒和仇恨,足以要了辰月教的命。
大教宗并没有屈服,早已组建的、属于辰月教的武装“缇卫”正式出动了。双方在天启城的夜幕下进行着残酷的绞杀,缇卫们掌握了杀人的许可和人数的优势,而天罗杀手们拥有更加精巧的技术。双方的绞杀蔓延开来,很快,原本不属于天罗的流浪武士被巨额的金钱收买为杀人者,而缇卫们也把队伍扩充到了近乎军队规模的七个卫所。
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愈演愈烈,传说诸侯们正在密谋联合,要推翻大教宗的统治,又有人说大教宗已经和北陆的新大君吕青阳达成协议,要一同拔起诸侯的残余势力。但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双方手里都不掌握优势的兵力,还无力在正面战场上兴兵挑战,而要依赖残忍隐秘的“杀手战争”先行耗损对方的斗志,为自己争取时间。
这场杀手战最后席卷了几乎所有权力组织,夜幕下的天启城里,奔行着黑影和血淋淋的鬼魂。
【CHAPTER2 夜浓】
第一章 楔子?刀耕
大胤圣王十年十月,天启。
还有一个对时。他觉得自己的手臂因为长时间的静止已经近乎麻木,于是极其缓慢地收紧复放松全身的每一块肌肉,仿佛一条沉睡中的蛇疏松骨骼,他必须防止自己的身体因为长时间的僵硬而迟钝。五个对时以来,他始终保持着这个要命的姿势。
他的十个手指细长而有力,精瘦的身躯整个蜷缩在一起,像是孕妇子宫里的婴儿,只靠手指和腿的力量将自己悬挂在牌坊的飞檐下。
这个牌坊身处闹市,因为长时间的日晒雨淋,昔日考究的琉璃瓦和彩釉早已脱落得七七八八,用作装饰的飞檐只斜斜飞出不到两尺,就偷工减料地完成了,在暴雨下连遮蔽都很难做到。
但是两尺对这个杀手来说已经绰绰有余。
谁也想不到这里竟然还能藏进一个大活人。杀手很满意自己选择的地点,从昨天深夜到凌晨,他一直隐蔽在这里,看着屋檐下的光影变化,听着外面由寂静到喧闹。
这次蛇一般的放松让他感到隐隐疼痛,肌肉僵硬太久了。本堂刺客里有过先例,有人因为身体长时间的过度收紧而再也不能放松,后半生只能佝偻着渡过。不过这些对他算不了什么,他轻轻活动了下右手,感觉那些锐利而诱人的丝线在手指四周轻盈地跳动,像自己饲养的毒蛇,温顺而致命。再过一个对时,他的目标将经过这里,那个掌握着缇卫第一所,最接近古伦俄的人。
本堂给他的情报简单、清晰而致命:缇卫一所卫长范雨时,印池系的秘术大师,气候干燥的秋天,是他秘术能力最弱的时候,也是他最容易被杀死的时机。杀手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双唇,天时地利再加上他自己,目标今日必死无疑。
他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一群步伐整齐的人正在逼近,虽然他现在的角度看不见,但是他知道那是一群黑袍黑甲的人。
秋末的天启,罕见的大风天,原本还有些行人的大街上,因为这队人的到来而迅速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呼呼的风卷着轻尘,显得有些萧索。
街角转出了十二名黑袍黑甲的缇卫,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腰侧是缇卫特制的黑鞘长刀。队伍正中是四个魁梧的从者,他们也身着黑色鱼鳞甲,环绕着正中的一个身穿黑袍的老人。老人的兜帽已经取下,露出一张苍老干枯的脸,双眼如深夜一般漆黑深邃。高耸的官帽下,须发皆白,灰白的长须垂了下来,直达腰际。他右手拄着一根细木拐杖,干瘦如树根的指节紧扣着手杖上精致的涡状花纹。
缇卫的一卫长范雨时,同时也是辰月的“阴教长”,拥有与身形不相称的强大力量。他的脚步沉稳而缓慢,原本被大风卷得四处飘飞的落叶在经过这只队伍的时候突兀地垂直掉落下来,然后被随之而来的黑色牛皮重靴踩成碎屑,发出干涩的响声。
飞檐下的杀手也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力,他轻轻咬了下自己的舌尖,迅速蔓延开来的痛楚让他恢复了镇定。他放松全身,让每一寸皮肤每一块肌肉都保持在最佳的状态。机会只有一次,必须一击即中。十二名缇卫依次在他身下经过,黑色的头盔上精致的纹路清晰可辨,他屏住呼吸,将原本明亮的双眼眯成一条线,整个人和四周融为一体,就算有人抬头望去,乍一眼也很难注意到他。
两名魁梧的黑甲从者经过后,范雨时那一头白发出现在他面前,就是现在!他在那一瞬间俯冲而下,像黑夜里的一只蝠,他的双手箕张,锐利的刀丝如一张飞扬的网遮住了所有空间。范雨时在那一刹那抬起头来,一瞬间,这个老人在那张陌生的笑脸上看见了死亡。杀手感觉到刀丝已经切入那些从者坚硬的盔甲,接下来就该是炙热喷溅的鲜血,他的全力一击挟着自身的重量,锐不可当。时间在他的感觉里好似变慢了,他可以感觉到那些精锻钢甲一丝丝碎裂,然后缓慢地飞离出去。他已准备好享受地倾听自己所带来的死亡之乐,却发现它迟迟没有响起。
缓慢,然后静止。原来不是他的错觉,他闪电般的动作确实慢了下来,最后静止不动了,他的眼能看,他的耳能听,他的手能发力,他的大脑能思考。
但是他动不了。
似乎根本没有看见范雨时吟唱,四周的水汽就以肉眼能见的速度迅速凝结在一起,最后变成了包裹他的一团水雾。周围的从者在瞬间的惊诧后反应过来,但是也一样被这团凝重的水雾包裹着,无法动弹。杀手用尽全力伸长手臂,左手的刀丝已经几乎拂上范雨时那满是皱纹的脖颈,但是他不能再移动分毫。他瞪大了双眼,整个人就这样被那团水雾悬挂在空中,面对着那个近在咫尺的老人。他觉得整个空间的水汽和他的冷汗凝结在一起,潮湿而沉重。
范雨时微微一笑,脸上的皱纹深似刀刻:“以凡人来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不甘心!杀手努力圆睁的双目边缘已经开始泛红,全身因为用力而青筋暴起,然而他整个人就如同陷在无比粘稠的浆糊桶里,根本不能移动分毫。
范雨时把细木手杖在青石地面上轻轻一磕,发出一声闷响。
那个杀手觉得身体一轻,然后前额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他整个人在空中炸成血花,碎裂的身躯和内脏掉落下来,被水雾混合着鲜血包裹着,缓慢地飞散出去,最后跌落在四周地上,炸开在青石板上。那潮湿厚重的街道又瞬间恢复了秋高气爽,只有满地的残骸证明着发生过什么。
四周的缇卫纷纷跪地,低诵神的奇迹,刚才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杀手从天而降,自己却被水雾包裹,不能动弹分毫。四个从者也跪倒在一边,为首的一人蛮族样貌,是跟随了范雨时多年的学生,许言是他的东陆名字。他的声音低沉:“学生无能,让老师受惊了。”
范雨时伸出枯瘦的左手,轻抚许言的头顶:“我们只要相信神所决定的命运,就能够无所畏惧。”
“学生明白了。”许言回答道。
“都起来吧,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范雨时抬起头,暗沉沉的天空下,风又开始起了。
天墟,观象台。
范雨时屏退四名魁梧的从者,孤身踏上最后一段石阶,沉闷的脚步声在偌大的石室里回响,高高在上的观象殿大门虚掩着,他能依稀看见里面缥缈的雾气。
门口站着一个黑袍的少年,整张脸几乎都藏在黑影里。少年伸手推开门,转头说道:“老师已经知道教长要来了,请进去吧。”清亮的声线被少年自己压低了,带上了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沉重。
范雨时微微颔首,从开启的大门走了进去。重重立柱支撑着大殿的穹顶,极深处,一个枯瘦的身影转过身来,银色的长发下,是一张消瘦的脸,本该是双眼的位置蒙着一块黑褐色的麻布。
星辰与月的黑幡下最接近神的代言人,古伦俄,静静地面对着范雨时。香炉的火光映照在古伦俄脸上,让这张脸有了一些生气,范雨时甚至能感觉到那两道透过麻布的锐利目光。
“今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连印池之阵都发动了,想来你也是遇见了棘手的麻烦。”古伦俄的声音低沉干涩,在宽广的大殿里回荡。
“麻烦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范雨时踏上一步,干瘦的左手伸进怀里掏出一叠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迹,“少保、三任鸿胪卿、大理卿、中散大夫、议郎、廷尉、南宫卫士令、小黄门侍郎、执金吾、司隶校尉……天启各类大小官员,迄今为止已有一百二十七人遇刺身亡,其余马夫从者无数。”
“天罗……真是群可怕的对手,连缇卫也无能为力么?”古伦俄问。
“如果没有缇卫,只怕这个人数还得翻上几番。”范雨时露出苦笑,“但是这些蜘蛛们天生就善于隐匿在暗处,我们所能剿灭的大多是从各诸侯国蜂拥而来的志士和下等贵族,真正被神之刀刃绞杀的蜘蛛爪牙们少之又少。”
古伦俄难以察觉地轻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大教宗明白就好,属下希望可以启动‘刀耕’。”范雨时双眼直视着那对被遮盖的双目,毫不退让。
“神之为刀,若耕若犁……”古伦俄有些感慨地顿了顿,“你去办吧,虽然早了一些,不过是时候彻底清除这些只懂得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毒牙了。”
曾经过往,我们又何尝不是藏身在黑暗之中呢?范雨时点了点头:“属下明白。”
“退下吧,以后的事情就辛苦你了。”古伦俄挥了挥手,“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随着他的动作,那叠名单簌地发出一阵脆响,然后化作粉末消散了。大殿里只剩下缥缈的檀木香气,古伦俄背过身去,消失在重重叠锦里。
胤匡武帝十年十月,天启的第一场雪很快就要降下了。白色的雪,能够掩盖一切,包括那些殷红的血。
又是这个梦。
他被悬挂在空无一人的陌生地方,骷髅塔上,白骨城中,放眼过去是白茫茫的雪野,那里是整个世界的尽头,存在和死亡的碑记。他赤裸身体,被死人的骨骼洞穿胸膛、手臂和双腿,整个人如同献祭给神的祭品,身体如被生生撕开般剧痛,却不能醒来。
这样的痛苦又将持续整整一晚,直到黎明。他对着雪野咆哮,他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没有人回答他。整个世界的活人都离他而去,他将在孤独和痛苦中渐渐麻木,身体在寒风中被慢慢剥蚀成尘埃,直至天地毁灭时,一同消亡。
醒来……或者……杀了我!他还是得不到任何回应,比死更可怕的事,莫过于你等待死亡,死亡却永不到来。
孩子,等待被救赎么?他第一次听见这声音,努力地睁眼,远远的一个黑影渐渐变大,直到完全清晰。一个老人穿着黑袍,须发皆白,手中握着一根细木杖。他是天地尽头孤独堡垒的行者,对着天空呼吸,在吊起他的骷髅塔下经过,目光落在无尽的远方。
孩子,等待被救赎么?
孩子,等待被救赎么?
孩子,等待被救赎么?
老人的声音如雷霆,如神谕,发聩震聋。他身上的剧痛消失了,温暖的触感包围了他。他啜泣着伸出手去,想要握住老人那双苍老干枯的手,像一只离群的鸟儿找到了家。但是他还做不到,老人的黑袍飞扬着,在雪野上远去。
你知道何处找我,只消相信自己的感觉。老人在天地尽头轻声说。而后他如雪化一般消失了。
漆黑的屋舍中,他整个人从床上坐起,冷汗淋漓,泪水横过面颊,回到了现实之中,身上的被子被汗浸透,在秋末的夜里平添了几分寒意。六年了,他第一次在这个相同而痛苦的梦境里看到了变化,他不知道那个老人是谁,也不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同一时间,一群人从相同的梦境中惊醒过来,脑海里都回响着同一句话。
孩子,等待被救赎么?
远方的太阳挣扎着撑破墨一般的天际,第一线阳光从山麓上洒下,古城里隐隐传来了几声鸡啼。
他做了决定,他必须找到那老人终结他的痛苦,否则他会被噩梦的痛苦绞杀。他有预感何处可以找到老人:
帝都,天启城。
范雨时睁开眼,彻夜的冥想让他有些脱力。当初播下的那群种子,现在能感应到的只有六十九人。比想象中的多一些,他有些欣慰地想。这些种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最终生效,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也能够给天罗重重的一击。虽然他们如踩在细丝上的蜘蛛一般,行事永远小心谨慎,但是他们一定想不到,辰月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支隐藏在黑暗中的毒牙,并且早就种下了足以毁灭他们的种子。越是隐秘的机构,从内部给予的打击就越致命。
门上突然响起几声轻响,“进来吧。”范雨时整了整黑袍,食指轻敲着膝盖。
推门进来的是许言,魁梧的身形跪在门口,“有人求见。”
“谁?”随着天罗愈演愈烈的刺杀行动,范雨时的行踪也隐秘了很多,能知道他这个驿所的人已经不多。
“学生不认识,他只是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许言的声音很平静,“‘我来了,救我。’”
比预期的还好。范雨时满意地颔首:“让他进来吧,我已经等了他很久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促进文化交流,本站整理收录的小说资源均源自网络公开信息,并遵循以下原则:
1、公益共享:本站为非盈利性文学索引平台,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收费性质的阅读与下载服务;
2、版权归属:所有作品著作权及衍生权利均归属原作者/版权方,本站不主张任何内容所有权;
3、侵权响应:如权利人认为本站展示内容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把该作品相关材料私信至站主或者发件到邮箱。经过核实后,本站将会在48小时内永久下架相关作品。邮箱tegw202@gmail.com
4、用户义务: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利用本站资源进行商业牟利、盗版传播等违法行为。
5、我们始终尊重原创精神,倡导用户通过正版渠道支持创作者。如对版权声明存疑,请联系我们进一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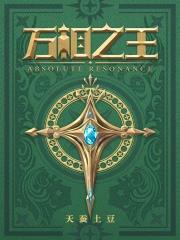


![《[最新]豪乳老师刘艳》连载 (1-9部35章+番外同人) 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uploads/2025/03/20250408195915145-《豪乳老师刘艳》1-8部120章-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jpg)















![表情[xiaoku]-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xiaoku.gif) 三十多兆的小说。。。
三十多兆的小说。。。![表情[tuosai]-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tuosai.gif)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