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武侠
武昌城内的荒地上,星星点点的破旧棚屋,排列成阵。
它是武昌的“脓疮”,却也是清贫小民遮风避雨的港湾。
楚王、金玉堂主、船帮把总、衡山剑客,他们角力于这一方土地之上。
——为利、为情、为钱、为欲。
而被裹挟进这场惨斗的孙大、孙二,他们最后失去了什么,又终于寻回了哪些?
一碗素面,一把锈剑,一个江湖。
这是两个失掉本心的孩子,重溯梦想的故事。
楔子
孙大和孙二是兄弟。
但生下孙大孙二的,应该不是同一对儿爹娘。
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孙大和孙二都是孤儿,谁也没见过自己的爹娘。既然都没见过,那么就不能说他们的爹娘是同一对儿,也不能说不是。
这两个半大的孩子,一个从东面逃荒而来,一个从西面逃荒而来。到了依山傍水的孙家村后,便在村西的一个破草棚里住下。他俩都没有名字,所以就都随了村子的姓,也就成了兄弟。
孙大爱吃,想做大明朝最好吃的面条。孙二爱闹,要当大明朝最厉害的剑客。
白日里,孙大会去田间垄头抓蛇、田蛙、知了、耗子以及各种说不清名字,却能胡乱烤了果腹的东西。
而孙二就拿着根木棍,出去找比自己块头大的孩子比武。
──打输了就滚回兄弟二人住的草棚,啃着焦糊得已经分辨不出物种的“食物”。
赢了就要半簸箕粗面当彩头。然后蹲在草棚下那口破烂铁锅前,等着孙大和好了面,下上满满一锅面条。
孙大从没喝过酒,不过他醉过。事实上,每当面条滚入水中,腾起的水汽扑到锅边探着头的孙大和孙二脸上时,孙大都会醉。
而孙二会饿,饿得不由自主地伸手,朝在开水中翻滚的面条捞去。只是每次孙二的手都会在与开水亲密接触的前一秒,挨上狠狠一记藤棘。
彼时孙二总会揉揉发红的手,开始纳闷孙大的这一招,怎么都比号称孙家村第一剑客的孙虎头还要迅捷。
一锅冒着热气的面条出锅不久,便被两个半大小子风卷残云般地分食殆尽。
草棚外的枯井早已被封死。吃完面的孙大舀起一瓢面汤,学着孙二的样子坐到井沿上。
天上冷月高悬,四围风鸣虫叫。
孙大和孙二,坐在井边,一人一口面汤,月下对酌。
两人谁也不说话,只是有时看看月亮,有时看看对方。
直到抬不起眼皮的孙二靠向孙大,直到抬不起眼皮的孙大,也靠向了孙二……
十一二岁的孩子,如同春雨过后的野草,一天天的疯长着。
来孙家村的第三年,孙二成了村子里最好的剑客,孙大也做出了村子里最好吃的面。
于是爱做面的孙大改名叫孙面,爱练剑的孙二改名叫孙剑。
也只是在一个与往常别无二致的月夜里,坐在井沿儿上的孙面捧着半瓢面汤,也不去看身侧的孙剑,只是静静地说道:“西边有最好吃的面,我要去西边。”
接过水瓢的孙剑砸吧砸吧面汤,语气里带上股淡得不能再淡的落寞。
“东边有最好的剑客,我要去东边。”
两人一起无言抬头望月,手中的水瓢传来传去,瓢中的面汤却始终也不见少。
直到墨黑色的天边挤出一抹鱼肚白。两人拍拍屁股上的泥土,一个向西,一个向东。
而最后被弃在水井边上的葫芦瓢,里面的面汤,还是没有喝完。
第一章
五年后,武昌城。
城北辞家巷后的荒地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破烂的棚屋。
骤起的寒风将盖在一个个棚屋上的毡布吹得噼啪作响,却吹不走空气中弥漫的腥臭。荒地上连绵起的座座棚屋,就蜷缩在武昌城内一角,却没有人将这里称为“武昌”。人们似乎只将它视作独立于城内的一块脓疮,随时都会被狠心剜去。
人们给这个脓疮起了个名字,就叫“麻子城。”
在辞家巷访云楼租住一间雅阁的高行周,此时就倚靠在窗边,闻着从“麻子城”飘来的酸臭味,遥望荒地上星星点点的棚屋发着呆。
五更未过,门外就传来了有节奏的敲门声,高行周似乎早料到有人深夜造访,悠悠地喊了声“进来。”
一个劲装男子推门而入,他进了门,也不看倚在窗边的高行周,就径直走到桌子旁,拎起桌上的茶壶对着壶嘴牛饮。
高行周蹙起眉头,不悦道:“明前的龙井,你就这么喝?”
“渴。”男子几口就将茶水喝尽,这才望向说话的高行周,“还有吗?没喝饱。”
“没有!就你这样子,打口井都得让你喝干了。”高行周不自觉地瞄了一眼男子腰间那块代表着“鬼影子”的鬼面玉佩,心中涌起一丝凉意,“让你杀的人,杀了吗?”
“没有。”
高行周双目圆睁,讶然道:“没有是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没杀。”劲装男子打个哈欠,语意慵散道,“马纪来武昌前,也算是江湖中成名的剑客了,功夫还在我之上。要杀他,总要找个合适的机会。”
高行周狠狠跺脚,怒道:“三天之内,我一定要看到马纪的尸首!他三番五次坏我好事,若不是他,‘麻子城’早就得以重建,也不会时至今日,还像个烂疮般戳在这里!半月后便是新楚王府的‘奠基大典’。我已跟楚王打了保票,此事若有差池,我便人头不保!这马纪不除,我如何心安?”
劲装男子随意地应了,便凑到窗前,学着高行周的样子,遥望不远处的“麻子城”。
天未破晓,居住在麻子城里的人们渐次醒来。锅碗瓢盆地敲击声、婴儿的哭闹声,加上偶尔掺进的声声犬吠,这些声音混在一起,代替着灯光,将无钱燃灯的麻子城点亮。
“你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吗?”劲装男子忽然问道。
高行周嘴角挑出一个骄傲的弧度,他抖抖金丝勾线,鎏金包边的锦袍,道:“是啊,我就是在这淌不尽的泥粪水里生,在这挡不住雨的木棚屋里长的!所以我发过誓,总有一天,我要把麻子城内的棚屋全部换作广厦!”
劲衣男子目光一转:“可麻子城里的小民怎么办,他们可住不起广厦。”
高行周冷哼道:“那又如何?活得了就活,活不了就死呗!世道就是这么个世道,有人坐在车上,就有人死在车辙下。你顾着这帮不长进的贱民,他们就永远不长进!穷,谁没穷过!穷还有理了吗?”
劲装男子也不与他争辩,只是望向窗外没头没尾地说道:“那是个卖面的。”
高行周一愣,顺着劲装男子的目光望去,见到从麻子城里延伸出的小路上,正走着个挑着面担的年轻人。
“卖面的有什么稀奇的?”
劲装男子耸耸肩,道:“没什么稀奇。”
高行周皱起眉头,不悦道:“我可把话挑明了,‘金玉堂’每年拿着几千两黄金供‘九子’挥霍,什么好处拿不到不说。就连你手下这么一支‘鬼影子’,都是我拿三百两黄金,才从‘螭吻’手中换来的。你要是这么点儿事都做不成,那我可得跟‘螭吻’好好说道说道了!”
劲装男子微微颔首,不疾不徐地离开了窗边:“两日之内,我定为你取马纪项上人头。”
高行周微一挑眉,怪声怪气地说道:“诚愿如君所言吧!”
劲装男子推门而出后,屋内的高行周冷笑一声,目光又不自觉地飘向了窗外。
夜色如洗,昨夜的一场冷雨,将狭窄的小路浸成一片泥沼。挑着面担的年轻人卷着裤脚,于泥泞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生生走出股世路难行的无力感来。
等到那年轻人终于踏上辞家巷后的青石板,目不转睛的高行周才终于回过神来,他无奈地笑笑,自言自语道:
“不就是个卖面的嘛。”
“有酒”酒肆的西侧,搭着一个破烂的棚子,草棚下挂着的布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个“面”字。草棚不大,将将能放下两套桌椅。
天光初开,狭长的街道上只零散地走着早起的行人。挑着面担的年轻人,足足走了大半个时辰,才从“麻子城”走到了自己的面摊。他将面挑放下,便开始起火烧水。水还未开,隔壁的酒肆里便走出个微微发福的中年汉子,坐到东首的桌旁。
年轻人迎到桌旁,笑道:“和往常一样?”
中年汉子伸伸懒腰,应道:“和往常一样。”
汉子的名字叫马纪,是隔壁有酒酒肆的老板。整个武昌城里,大大小小的酒肆不计其数, 可这有酒酒肆却与其他的酒肆不同。
不同就在于这有酒酒肆,只有酒。
虽是有酒无菜,但有酒酒肆的生意仍旧是出奇的好。许是因为老板马纪自酿的酒水的确醇香,又许是因为,太过平凡的人,总以为去了不平凡的酒肆喝酒,自己也就能变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平凡了。
当然,总会有不识趣的酒客喝了几两小酒,便叫嚷着让马纪去弄些饭菜,但大多时候他们嚷着嚷着,也就瞥见了挂在墙上的长剑,也就不嚷了。
听街尾的刘二说,这马纪曾在衡山学艺,当年在江湖上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因他一手衡山绵剑剑意绵长悠远,还得了个外号——“蛛丝”马纪。至于这么一号人物,怎么就沦落到武昌城里贩酒,刘二也说不清楚。
年轻人将一碗冒着热气的素面端给了马纪,便坐在一旁的桌上扒着蒜头,偶尔还抬头偷瞄马纪腰间挂着的长剑。
“怎么?喜欢这剑?”
吃着面的马纪连头都未抬,却发现了他的小动作。卖面的年轻人听了马纪的话,微怔一下,便憨笑道:“从没见您带着剑出来,有些好奇。”
马纪吸溜一大口面条,头一次仔细打量眼前的面摊老板。
虽说靠着小本买卖营生的年轻人,多少都显得有些落魄,但他人还长得还算周正,在外奔波得久了,皮肤也被阳光烙上一层健康的麦金色,让人打眼望去,便觉得踏实。只是他的脖颈上横亘着一条吓人的长疤,似是经历过什么厄运。
马纪咽下嘴中的面条,道:“非常时期,提防些小人。”马纪说完这话,见到面摊老板眉头微皱,知他会错了意,连忙道,“我不是说你,可别瞎在这儿对号入座,我得罪的虽是小人,但也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他话一离口,便觉越描越黑,索性洒然笑道:“小老儿我不会说话,你就权当我放屁。”
年轻人也不在意,只是叹了口气,道:“是因为征地的事吧?唉,金玉堂盯着麻子城这块地也有好些年了,我们这些小民之所以还未流离失所,说到底全靠马先生您的帮衬。可听说这次是楚王看上了麻子城……”
年轻人嗫嚅半响,似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方才续言道:“马先生,要我说这次您就别管了!各有各的活法。您没必要为了我们这帮不相干的人,惹祸上身。”
马纪摇了摇头,伸手拍拍腰间墨色剑鞘,轻描淡写地说道:“从师父手中接过这把剑后,这世人于我,便没有不相干的了。”
年轻人听了这话,如同灌了口陈年老酒般涨红了脸。他狠拍下桌面,低喝道:“这句说得好!”年轻人说完这话,目光搭到马纪腰间宝剑之上,似是想到什么往事,面色忽地转暗。
马纪见状蹙眉问道:“怎么了?”
年轻人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强笑道:“没什么,忽然就想到些旧事。”
马纪见他黯然神伤,也不忍细问,只是挑起一绺面条,说道:“我见你怕也是个爱剑之人。你这根骨嘛,不算好,也算不得太差。这样吧,你若是有意,改天我倒是可以指点你两招,权当强身健体。”
年轻人双目一亮,连连道谢。一碗素面吃完,年轻人说什么也不收马纪的钱,马纪拗不过他,也就不再坚持。
临走时马纪忽然问起年轻人的姓名。
那卖面的年轻人嘿嘿一笑,打趣道:“我乃孙家村第一剑客,孙剑是也!”
第二章
六年前在清安镇输给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梁震维后,马纪心灰意冷,托人给衡山的掌门师兄许远山捎了个信儿,便归隐于武昌城内,当了个贩酒翁。
虽是江湖渐远,但马纪胸中一腔侠义却未失半分。他刚来武昌时,恰逢武昌府衙的官差大肆驱逐麻子城内的住民,住在麻子城内的苦哈哈一时无家可归,武昌船帮总把头刘水生几次带着人去衙门口闹,都被官兵镇压。
最后还是马纪略施小计,弄到了武昌府尹孙文年收受金玉堂贿赂的罪证,麻子城内的苦哈哈们这才得以重归家园。
之后的几年里,金玉堂对麻子城这块肥肉仍未死心,但没了武昌府的支持,数次动手,都被马纪和刘水生从容化解。肉没吃到,反倒弄了一身的骚。
今年年初,就藩已有三年的楚王忽要兴建新楚王府,在金玉堂堂主高行周的游说下,武昌府工房终是选定了麻子城这块地皮。至此,高行周算是握住了一把必胜的牌。
听闻此事的马纪与刘水生几次相商,都是一筹莫展,眼看着离楚王府的奠基大典只有不足一月,两人嘴上不说,心中却俱感此次怕是已无力回天。
早上马纪从孙剑的面摊吃过了面,回到酒肆,连打的板都未及拆开,门外就来了个苦哈哈,言刘水生捎来口信,约马纪巳时在梨花楼见面详谈,似是想到了什么办法。
马纪寻思着左右无事,匆匆洗了把脸,便先到了梨花楼。梨花楼的掌柜与马纪相熟,见他来了,连忙吩咐小二将马纪带到楼上雅间。
桌上的茶换了一壶又一壶,快到午时,也不见刘水生赶来。马纪心念刘水生管着码头数百的苦哈哈,难免有事耽搁,也就未着急。只是临近正午,酒楼正是上客时候,马纪也不好独占着一间雅间耽误人家生意。便叫过小二,要换到二楼大厅散座,将雅间让出。
小二正被几位嫌弃散座嘈杂的客人责难,听了马纪的话,连忙千恩万谢地给马纪换了个靠窗的座位。
马纪刚刚坐下,便听到邻桌传来一阵爽朗笑声。他侧头望去,见到邻座坐着几个壮年男子,持枪带棍的,每人都捧着个酒碗痛饮,间或说些没品的笑话。
马纪见几人面生得紧,一时偷偷留心。
邻座吵闹,马纪倒是不甚在意,只是他被几人桌上飘来的酒香勾起了馋虫,便也要了一壶老酒,自斟自饮。邻座那几人喝到兴起,便开始臧否江湖人物。几人说得有趣,马纪也就不自觉地旁听起来。
桌边立着一根铁枪的粗壮汉子首先便提起使子母阴阳剑的“乌衣”王隐岫,却被身侧的蓝衣男子以王隐岫为人太过阴鸷,没有宗师气度而打断,他既而又说到“蓬山云剑”赵远策,言到此人剑法如一峰孤绝,睥睨四方,才是当今江湖用剑第一人。
身后背着个细长包裹的鹤发老者也抽空插话,言语之间,还提到了当年以一套不入流的剑法败尽三山五岳各路名家的“琅嬛剑典”梁震维。几人说到他声名正盛之时,却忽而匿迹,还不禁唏嘘一番。
马纪冷不丁听他们说到害自己赧然弃武的梁震维,轻叹口气,狠命灌了口老酒。
三人争论不休,粗壮汉子眼见自己落了下风,便望向对首的那人,言语恭敬道:“吕先生,咱们四人之中,您武功最好,见闻最博,您也给咱说说,在您心中,这天下第一剑客,该是哪位大英雄?”
马纪循声望去,见那久不说话男子腰间别着把白玉长笛,又听粗壮汉子叫他吕先生,便隐隐猜出此人身份,不禁就是一皱眉头。
那姓吕的男子面上含笑,言语中却不胜落寞:“我便是说了,你们也不会信。”
鹤发老者道:“您还未说,怎知我们不信?”
“我若说是在暖城凌虚一指,便有万剑入空的青城侠少陈拙,你信也不信?”
蓝衣男子尴尬笑道:“吕先生说笑了,这些神乎其神的江湖传言,自是大不可信。”
被他称作吕先生的男子也不争辩,只是默默地饮了口酒。邻座几人一时有些尴尬,倒是静了下来。
当年九命郎安不换在暖城建立“无处不均”的侠义城,引得朝廷侧目。传闻四五年前,三万“百罪骑”西出阳关,直奔暖城。侠义师在城外设伏,两军遭遇,俱是死战不退,这一场好战连延数日,战至刀摧甲裂,箭尽弓折。
大战过后,三万“百罪骑”埋骨黄沙,侠义师也是十之去九,连统领侠义师的九命郎安不换都将星西陨,落得个马革裹尸,但惨胜也是胜了,这些年朝廷忙着北征残元,也就无暇西顾,暖城在“新帝”赵出秦的治理下,隐隐成了那些亡命之徒心中的“桃源仙境”。
至于那男子口中青城侠少的故事,马纪也听闻过一二,大概说的就是两军僵持之时,忽有一白衣少年驭万剑破阵,助侠义师取胜。
马纪不屑地摇头,心道沙场是将士的沙场,可这江湖,终归还是说书人的江湖。
马纪正在这儿默默唏嘘,却见到数人众星捧月般,拥着位华服男子上了二楼,那男子四十岁上下,方面大耳,面上还隐约能见出年轻时剑眉星目的模样,只是身材却早已走了样。
马纪眉头微皱,倒是没想到能在此处碰上“金玉堂”堂主高行周。
高行周上了二楼,一眼便看见了坐在窗边的马纪,他嘴角挑出一个轻蔑的弧度,带着一众随从径直走到马纪对面,大喇喇地坐下。
马纪头次见到高行周带了这么一大帮随从,不禁冷笑道:“高老板好大的排场。”
高行周皮笑肉不笑,微微拱手道:“马先生,好久不见啊!”
马纪泠然应道:“本希望能更久的。”
蓝衣男子察觉到邻座气氛有异,又见那锦衣胖子身后浩浩荡荡地跟着十几个随从,他似是看不惯有人仗势欺人,忽然就朝着马纪一拱手,问道:“朋友,可是遇到麻烦事了?”
马纪闻言心中一暖,他不理一脸诧异的高行周,便朝着邻座众人回礼道:“多谢兄台了!些许宵小而已,在下还应付的来。”
那蓝衣男子此刻方才瞥见马纪腰间长剑,便微微颔首,不再多言。高行周身后的随从却猛然喝道:“姓马的,你说谁是宵小!”
马纪还未答话,高行周倒是朝身后的随从摆了摆手,含笑道:“马先生若是自诩为英雄,那高某人当回宵小又何妨?只是马先生可曾想过,你这英雄,救得都是些什么人?”
马纪咂口酒水,道:“不劳高老板费心。”
高行周也不管马纪是否愿听,张口说道:“午时前在码头赚足三十文钱,五文钱拿去泡池子,五文钱拿去听曲,三文钱吃碗烩面,五文钱买壶烧酒。耍到申时,十文钱买几两粗面,半把烂菜叶,连着口袋里剩下的两三文钱,带给老婆孩子。这就是你要救的苦哈哈。”
马纪眉头微蹙:“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要说什么?我要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知道他们的弱是因为穷,却不明白他们的穷,只是因为懒!你千辛万苦去保那麻子城,你以为你保的是给他们遮风挡雨的窝?错啦!你保的是那帮懒鬼不思进取的根!”
高行周目光灼灼,直望入马纪双眼:“谁都愿如你一般,做个行侠仗义的英雄。可我不愿,我只愿做个抽筋扒皮的恶鬼,因为我抽的是这武昌的懒筋,扒的,是这武昌的癞皮!”
高行周寥寥数语,可算掷地有声,不仅马纪一时无语,连邻座四人都沉默起来,似是在细品高行周话中意味。
马纪沉默半晌,方才应道:“道不同,不相为谋。高老板若是来游说在下,便不必多费口舌了。”
高行周神色转缓,含笑道:“只是闲话几句,马先生不必挂心。”说话间小二已端上一壶新茶,身后的随从接过茶壶,斟满高行周面前茶杯。
高行周吹去杯上热气,故作随意地问道:“刘总把头与马先生不是约在午时吗?他这时候还未到,该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吧?”
马纪闻言如遭雷殛,面上却仍是不动声色:“高行周,你什么意思?”
高行周轻咂口茶水,也不言语,只摆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
马纪隐感不妙,他长身而立,口中语气愈发森冷:“高行周,你该明白,你若是害了刘兄,便是天涯海角,你也难逃我手中长剑。”
高行周摇头叹道:“怕只怕害了刘水生的,不是我,是你。”
马纪冷哼一声,再不多言,他离了梨花楼,便直朝码头奔去。邻座几人似乎也被高行周的一席话扰了兴致,蓝衣男子结了酒钱,几人便也渐次离开,那姓吕的长笛客坠在最后,临走时还回头望了一眼邻桌的高行周,目光炯炯,似有深意。
高行周透过窗户向外望去,直到马纪的身影慢慢溶于长街尽头,他才开口说道:“孙面,你要我给你个机会近处观察马纪,机会我已给了,倒不知你都看出了什么?”
高行周身后人群骤然分开,一个消瘦男子从人群中走出,坐到高行周侧面,这人朗目高鼻,竟是今晨在访云楼与高行周见面的劲装男子。
这叫孙面的男子伸手就要去拎桌上的茶壶,却被高行周一把推开。
“刚沏的茶!对着茶壶喝就不怕烫死?你想喝我给你倒!”说着便拿过桌上茶盏,斟了一杯香茗与他。
“别净顾着喝!问你话呢?你都看出了什么?”
“还能看出什么?”孙面吹开茶盏上腾起的热气,不紧不慢地续道,“无非就是死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促进文化交流,本站整理收录的小说资源均源自网络公开信息,并遵循以下原则:
1、公益共享:本站为非盈利性文学索引平台,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收费性质的阅读与下载服务;
2、版权归属:所有作品著作权及衍生权利均归属原作者/版权方,本站不主张任何内容所有权;
3、侵权响应:如权利人认为本站展示内容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把该作品相关材料私信至站主或者发件到邮箱。经过核实后,本站将会在48小时内永久下架相关作品。邮箱tegw202@gmail.com
4、用户义务: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利用本站资源进行商业牟利、盗版传播等违法行为。
5、我们始终尊重原创精神,倡导用户通过正版渠道支持创作者。如对版权声明存疑,请联系我们进一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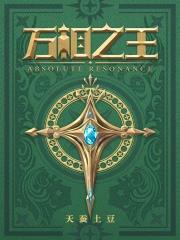


![《[最新]豪乳老师刘艳》连载 (1-9部35章+番外同人) 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uploads/2025/03/20250408195915145-《豪乳老师刘艳》1-8部120章-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jpg)















![表情[xiaoku]-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xiaoku.gif) 三十多兆的小说。。。
三十多兆的小说。。。![表情[tuosai]-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tuosai.gif)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