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悬疑 推理
城乡迁徙,世纪跨越,罪人眼中见到什么?
2014年秋,橘子洲尾的沙滩公园正在举办人气沸腾的音乐节。夜幕降下,严密的安保区域内,一具尸体出现得不可思议。岳麓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迅速理清线索,次日清晨将疑犯抓捕。
他是谁?怎么做到的?原因为何?
证据明摆在眼前,疑犯的沉默却让案件变成故障钟表,齿轮无法咬合,只能不停将时间往回拨。
第一章 回到分歧的路口
1
年轻的保安沿着江岸走,仰起脖子,望见蚊虫在飞。
那些模糊又快速移动的黑点是摇蚊,曾有人教他不要怕。那人说摇蚊只是对二氧化碳敏感,所以喜欢在人的头顶绕着飞,尤其是人在流汗发热的时候,排出的二氧化碳多,它们来得就多。但摇蚊不咬人,只是在进行一种名为“婚飞”的群交。
群交的摇蚊忽然闪出一阵星星点点的反光,像是烧柴的时候还未燃尽的火灰,他才看清楚这支队伍是多么庞大而密集。恐惧感渗进他头皮,令他不禁一抖身子,腿脚加快步伐。刚才那束亮光是从远处舞台射过来的,瞬间照明了江面上翻滚的黑暗细浪,还未看定它又移动了,划向舞台下那群观众,把一张张焦急等待的面孔照得亮眼。
下一支乐队已经登台,鼓手拿鼓槌随便敲了几下试音,躁动的人群就开始兴奋地喊叫。
橘子洲直到落日之前还忍受着太阳的烘烤,夜晚有了江风本该凉快些,但现场实在太拥挤,人们只好呼吸着彼此身体散出的热气。有个脸上涂了几抹油彩的牛仔短裤女孩,骑在男朋友沁着汗水的脖子上,把方才还在挥舞的双手收回嘴边,聚成喇叭状,大喊了一句:“欧珈源我爱你!”
“我也爱你们,长沙的朋友,”台上的乐队主唱手持拨片,在吉他上轻轻扫弦,凑近麦克风,清嗓之后,用很巧妙的方式报出了即将要演唱的歌名,“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1]?”
欢呼、灯光、前奏、烟雾特效,气氛上来了,台上的乐队领着台下的人群躁动起来。舞台两侧巨大的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摇臂摄影机拍摄的实时观众影像和色彩缤纷的炫目动画,以及“2014星城音乐节Star City Music Festival”的波普风格艺术字logo,与草地中央聚光灯照耀下的音乐节实体招牌遥相呼应。
在那实体招牌雕塑附近,游荡着一位胸前垂着工作证、身穿宝蓝色志愿者T恤、用火钳去夹空饮料杯的中年女人,她明显比旁边身穿“岳麓环卫”橙色反光马甲的老头干得更为卖力。
“人气旺呢……”女志愿者忍不住发笑,同清洁工老头大声攀谈,“人气好旺!如今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不容小觑!”
“不容什么?”清洁工人把脖子伸向她,年纪大了,有些耳背。
“就是不容小看的意思!”中年女人提高音量,咯咯笑得苹果肌油光发亮,“今天好热闹吧?这个演唱会,是我投的资!”
老头打量了她的衣着,撇着嘴哼笑了一声,显然不怎么信她,弯腰去捡下一处垃圾。
“不骗你呢,爹爹[2]!我投了三万,我们一起投的!”女人用火钳指向不远处几个和她穿着同样T恤的志愿者,说这叫众筹,一种投资新模式,投得越多,回报越多,发起人给他们下了保证的,等到明年,起码可以翻到十倍!她又问老头有没有钱,趁现在还有少量机会,可以带他一起投。
环卫工人用力摆了摆手,和她保持距离,装模作样地提高了音量,说这里太吵了,她说的什么听不清楚。
刘勇并没有听太清楚电话那头讲的什么,刚才音乐确实太吵了,隔那么远,鼓和贝斯的低音轰得人心脏发颤。
同事抹着额头的汗问他,那边怎么说。
“在路上了。让我们低调点,先控制好现场所有的知情人员。”他顺口问同事,这一点能否办到。
同事回答应该没问题,这要多亏了当时那个武警兄弟,考虑周到又灵泛。
要不是之前那个巡逻的武警正好出现在茶社门口,又在接到报案后,一边做好现场的稳定工作一边上报警情,事态肯定要严重许多——音乐节有人惨死的事,恐怕早在那群热闹的观众里传开了。
“走漏风声造成恐慌就完了,这么多人,最怕发生踩踏事件啊。”
刘勇站在警戒线外,不停举起矿泉水瓶喝水,脸上透着烦躁和紧张。才过了半分钟,他又拿起手机看时间,向身边的同事埋怨,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听的是些什么玩意儿。
同事站累了缓缓蹲下来,附和着说,看他们那么开心,放肆叫、放肆跳的样子,就感觉和茶社里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形成鲜明对比,有点瘆得慌。
刘勇感叹:“那人是造了什么孽,死这么惨。”
岳麓分局治安管理大队一个多月前接到这次音乐节的安保任务,刘勇没少带着同事们加班赶夜。尽管橘子洲上常年各种文化活动报批频繁,局里早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这种上万人的大型活动,谁也不敢保证能杜绝极端事件的发生,仍然需要细致的安保预案来未雨绸缪。
敦促活动主办方组织了四百多个安保人员维持秩序,调用了一百多名警力巡逻盯梢预防突发事件,安插了三十几个便衣在人群中见机行事,进场安检层层过关、处处设防,演出区域全封闭管理,别说危险品,就连用玻璃瓶子打架斗殴的危害性都考虑在内,只准许售卖一次性纸杯装的酒水饮料。
结果呢?却发生了如此骇人的凶杀案件。
“来了。”
刘勇走了下神,同事指给他看,一辆湘A牌照的红色轿车,领着一辆黑色商务车正朝着这边驶来,车灯刺眼。
“哐哐”几声开关车门后,背着铝合金箱子、穿着便衣的痕检技术人员和法医下了车,二话不说,快步走进茶社。
林立莲身后跟着几个刑侦大队的同事,来和刘勇打招呼。他告诉刘勇,杨局也在过来的路上了,火气有点大,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又说今天这种情况,之前可从没遇到过,凶犯这么嚣张,在这种场合犯事,很有可能再次作案。
林立莲看了看舞台那边热闹的人群,悄悄拉刘勇到身边,告诉他这种情况,得赶紧交代手下的人都紧张起来,随时准备应对紧急突发事态,市局那边也在组织更多人马赶过来。
刘勇叹了口气:“林队,麻烦刑侦的兄弟们了,帮忙早点解决。”
林立莲拍拍刘勇的肩膀称应该的,邀他进去详谈。
“对了,我手下有个小年轻,玩乐队的,今天正巧在这里搞演出,我打电话让他先过来的,来了吗?”
“罗门是吧?我知道他。来了来了,已经在里面做事了。”
林立莲一边带人往茶社院子里走,一边听刘勇讲大致的情况。
死者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名叫黎万钟,死在茶社二楼的包厢里面。
几名刑警抬起头,这间开在橘子洲尾沙滩公园的“橘洲故事”茶社,正如刘勇形容的那样,面积不大,结构也不复杂,因为是大落地窗的设计,视野通透。五六处散客桌椅都摆在室外木栅栏围起来的院子里面,建筑内一层有四个卡座,二层有两间包厢,室内有什么都看得比较清楚。不过案发的那间包厢,已经拉上了枣红色的窗帘。
“本来这两天大型演出,茶社不对外营业,但是黎万钟的这家‘欢聚网络’公司说要包场用作员工休息室。
“包场不算向观众营业,不违反我们安保预案的规定,场地方那边报批,我们也就同意了。
“结果今天,这家公司的老板就出事了。”
刘勇几句话语速很快,意思也明了。
林立莲问这家欢聚网络公司是做什么的。
“主办方那边说,是一家众筹网站。”
刘勇告诉林立莲,这家公司是本次音乐节比较小的一个合作方,提供了点资金,来换取少量的现场广告位置。另外,还免费提供了两百个左右的志愿者,在现场帮忙做些捡垃圾、发放小礼品和引导观众一类的志愿者工作,可以顺便宣传他们公司的众筹产品。
“众筹啊?最近打这个名号的诈骗和传销挺多。”林立莲在茶社门口停下脚步,吩咐身边的刑警小胖,打电话问下经侦大队那边的同事,有没有关于这家公司的案底和投诉。
刘勇等林立莲吩咐完,又带他去见坐在卡座沙发上的几个人。
其中一个黑色职业装、绾着发髻的年轻女孩拳头握紧放在短裙上,腮帮用力咬出了僵硬的轮廓,眼神呆板,脸色发白,看样子被吓得不轻。
刘勇告诉林立莲,她是最先发现案情的人,是在这家茶社打工的服务员。
当时,她正想起来给死者添开水,才带了热水瓶上楼去,敲门没人应,开门却看到尸体和一大摊血,吓得要死。
“林队,经侦那边的人查过了。这家欢聚网络公司目前没有案底;投诉和纠纷,我们岳麓区下面没有。另外这家公司注册在星沙,已经在往市局支队那边问了,有结果了会马上通知我们。”微胖的刑警插了一句。
“他们真查了?怎么这么快?”林立莲扭头狐疑地看向小胖。
“他们说罗门十来分钟前已经打电话问过这事了,市局那边的要求也是他提的。”
林立莲“哦”了一声,请刘勇继续说。
“接下来,另外几个在一楼的公司员工听到她叫,就上去看,都被吓着了,商量着报警。这位穿蓝衣服的志愿者是他们欢聚公司的人,打了110接警中心。这位穿白衣服手上戴串的,是茶社老板,跑出来想找我们执勤的民警,出门正好就遇到一位巡逻的武警兄弟,他帮忙掌控了现场,然后通知了我们。”
“当时现场的人就这么几个是吧?”林立莲仰头扫视了一下卡座那边,用嘴唇默默从一数到七。
刘勇旁边穿制服的武警回答就这七个,称他们都没有进包厢,也很配合工作,就是场面有点血腥,都有点受了惊。
“好,情况大致了解了。我先上楼看看现场。现在情况复杂,演出还没有结束,凶手再次作案的可能性也不小,你手头安保的指挥工作应该还挺多的,要忙就先去忙,这边先交给我们,我们随时保持联系,行吧?”
刘勇和治安管理大队的同事说好并转身离开,但脸上仍挂着担忧。
林立莲穿上鞋套,带人上楼,喊了罗门一声。
穿着狰狞紫色机械怪兽头印花T恤的年轻人举着一双橡胶手套回头,答应后走过来开始汇报情况。
“死者叫黎万钟,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板,更具体的社会关系在找人问了。”
“死的时候人脸朝下倒在茶几上,具体死因还得等法医做详细检查来下结论,不过基本能确定,就是脖子上的切伤致死。颈动脉大出血,流了一地,我观察了一下,尸体脖子上没有试探性的平行切痕,自杀这么利索的不太可能;但如果是他杀的话,一刀割喉,”罗门划动手指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手法也算非常专业了。”
“林队,我稍微补充下,”包厢内,叉开腿蹲在地上检查尸体的男法医说,“我认为他杀的可能性极大。除了创口很深,目前发现两侧颊黏膜腮腺附近有被牙咬伤的情况,另外颊面、鼻部皮肤有瘀痕,都不应该是死者自己造成的。他杀的话就比较好解释,死者被害时,凶手先是从身后架着他,用很大的力气捂住了他的嘴,然后迅速往脖子上抹了一刀,手法确实挺熟练的,极有可能是个狠角色、惯犯。”
罗门从地上的取证袋中,找出一把凝着血渍的匕首给林立莲看。
“但是有个疑点,专业惯犯作案的话,应该是做了充足准备的,现在他又把凶器留在了现场,这就很矛盾了。”
林立莲问有没有指纹。
罗门说凶器上有一些不怎么完整的指纹残留,在等技术做处理。
林立莲低头陷入思考,罗门继续说:“死亡时间还得等法医做确认。但就现场问到的情况,这个茶社的服务员最后一次来包厢见到死者,是下午6点五十几分,人还活着,等她7点半左右再过来发现尸体,中间相隔大约半小时。”
“那作案时间肯定就在这半个小时以内。这段时间进出这间茶社的人多吗?能不能排查出来?”林立莲环视四周,抬起手指,指着墙角对着楼下大门的摄像头问,“那个监控看过了吗?”
“监控问过,关了。”
“关了?”
“楼下的茶社老板说,关监控还是死者黎万钟自己包场时提出的要求。说是怕泄露他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罗门摇摇头,说问了楼下这家公司在场的志愿者,他们也一头雾水,没问出个所以然来。
“周边我们自己布的安防监控呢?”一位刑警同事提醒。
“刚问过橘子洲派出所了。派出所那边反馈说监控坏了不少,”罗门告诉他,“能用的几个都离得比较远,他们正在派人去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迹象。不过这种大型演出人员太多了,一时半会儿难度很大。”
“坏了?”林立莲皱起眉头,疑惑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坏了。
“橘子洲派出所给的说法是,昨晚很多监控都坏了,很有可能是传感器烧了。今天其实是音乐节第二天,昨天已经演过一天了。他们查了记录,说是从昨天傍晚6点多开始陆续烧的。”
派出所说已经打了报告上去,等上面过审批了安排承包商来修还要几天。罗门用自己玩乐队的舞台表演经验分析,推测是到了晚上,大牌乐队陆续登场,为了造舞台气氛,那些激光效果一多,晃到了监控摄像头的传感器,就给烧了。
“激光可以烧掉监控器?”刚才那位提安防监控的同事再次发表了自己的想法,“那岂不是任谁拿个激光笔就可以搞坏事了?”
“小型激光笔肯定不行,功率太低,但是舞台激光的功率高。我有朋友是摄影师,偶尔会来现场给我们拍些演出照片,有次相机的CMOS[3]就给舞台激光烧了。”罗门回答他。
林立莲点点头,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重点。
罗门称还有个疑点感觉很重要,就是这个包厢的窗帘。
根据楼下服务员的说法,她看到死者遇害前亲自把窗帘全部拉上了。服务员觉得这间包厢灯有点暗,问了他这样会不会采光不太好。他当时还和服务员开玩笑说当老板的采光不重要,隐私才重要。但是很奇怪——发现尸体的时候,他们看到窗帘全部都是拉开的,好像在故意给人看一样。
“现在窗帘是我们自己人拉上的吧?”
“是的,这么大落地窗,打开窗帘里面有谁在干什么,几乎能一览无余了。好在因为视角的关系,从楼下往上看,看不到地上的尸体。治安管理大队的人拉上的,怕外面音乐节的观众看见在做现场勘查,引起恐慌。”
“好,我明白了。”林立莲问今天音乐节还有多久结束散场。
“10点多最后一支乐队演完,基本上就要散了。”罗门看看手机时间,说现在8点,还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目前凶手是在安保区域内,还是已经离开现场,很难讲。
“好,时间很紧。”林立莲一击掌,提醒大家集中精神听。
“情况你们也看到了,很不乐观。如果凶手还在现场,随时会有再次行凶害人的可能。早知道他的身份,早抓住他,早放心。”他开始做动员,然后安排任务。
“法医和痕检就不说了,这个案子有多紧迫你们明白。现场的蛛丝马迹,指纹、鞋印、毛发、水杯上可能存在的唾液斑,所有能提供嫌疑人身份信息的技术手段,都要尽快出结果,我在这边陪你们。这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凶手的准确身份,只有搞清楚了,我们才能有的放矢。”
“除此之外……”林立莲举起四根手指,一根根往下弯,“我刚才在脑子里面转了一下,觉得有几个问题很关键,分配一下,你们去做。”
“第一,死者的人际关系,经侦那边的对接,还有现场公司志愿者的背景调查,哪些人最有动机,务必搞清楚,这个小胖负责。
“第二,凶手抵达和离开现场的路径,还有可能的去向。我说两点,一是死者身边出现过哪些人很重要;二是结合现场情况和刚才法医说的那种贴身割喉的姿势,凶手很可能穿着血衣,问问有没有目击者。不过要注意问的方法,千万不要泄露案情。张伟、杜然负责。
“第三,凶器是开刃匕首,这么明显的管制刀具,现场安检又是按照那么严的治安管理标准,凶器到底是怎么带进来的?罗门,你对音乐节的安保最熟,把现场掌握的情况交接给我之后,就去负责这条线。
“第四,这个沙滩公园,不是第一次作为音乐节场地,往年怎么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监控损坏案例?我认为很不正常。罗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舞台激光,昨晚监控大面积损坏的时候,是谁在控制,和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弄清楚。这个浩南负责。”
他双手轻抚,问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换来几句异口同声的“明白”。
“明白了就散,”林立莲声音并不大,也没有多少情绪在里面,却透出一种不容辩驳的紧迫,“我给一个小时时间,今晚9点之前,刚才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要出结果。”
刑警们默默转身向楼下走,一个个面色如铁。
茶社外舞台的方向,传来声音玩具乐队隐约的歌声,“你站在最高云端之上,俯瞰卑微生命,注视着我们的一切,然后说随它去吧……”[4]
从气氛紧张的“橘洲故事”走出来,望向草地那边躁动的人群,张伟和杜然不约而同地叉腰叹气。
他们站在茶社门口因镇流器故障而变得暗淡、不时轻微闪动的白色荧光灯招牌下,眼睛却盯着舞台那边炫彩斑斓的灯光特效出神。音响震天,年轻人们又唱又闹的,火热而奔放,兴奋极了。此刻,这里的死亡他们不知情,也就与他们无关。
找茶社内的几位做过笔录之后,再仔细想想林队布置下来的任务,其实颇有难度——张伟揉了揉脸分析,要摸清凶手的身份,抵达和离开现场的路径,最好先盘点出案发前后,都有哪些人在茶社出没。
杜然不作声,张伟就继续讲。
这间茶社被黎万钟的公司租用为休息室,除了在场的两位服务员,早先只有“欢聚网络”的员工进进出出、饮水休息、存取传单和广告礼品物料。如果一直这样,那么也许只要在公司员工之中做排查就能找到人了。但是从昨天的演出后半场开始,因为音乐节人气火爆,主办方安排的几台流动厕所车外人龙越来越长,偶尔会有些尿急的人走进茶社找厕所。
这些外面进来上厕所的人,就让茶社的人员流动变得复杂起来。
根据茶社服务员和欢聚网络员工的说法,昨天下午,员工们起初是不允许这些找厕所的外人进茶社的。后来正好被从包厢下楼出来的老板黎万钟撞见了,黎万钟当即批评他们思想觉悟不高,太过自私。
“来做志愿者服务,怎么能没有一点志愿者精神?”
黎万钟让员工们不要阻止外面的人进来使用厕所。自那时起,进出茶社的人员才开始变得复杂。
茶社厕所的位置在一楼卡座与二楼包厢之间,楼梯的转角。不分男女厕,但是有两个独立的厕位。
来当志愿者的员工说那些进来上厕所的人“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平均四五分钟一个人肯定是有的。也有上大号的时候,门口排三四个人的队,有人实在等不及了,又出去找别的厕所了”。
茶社内的员工,主要是处理志愿者物料的分发和记账的工作,也不算清闲。那些上厕所的人来来往往,多了之后,也就没有再去特地留意上楼下楼的都有谁。
于是,很有“志愿者精神”的黎总怎么死在了二楼包厢里边,也就无人知晓了。
笔录没有得出什么太有价值的重要线索,两人的情绪也都有点低落。
张伟想缓和一下气氛,碰碰杜然的胳膊,让他猜猜舞台那边有多少观众。杜然想都没想,就回答不知道。
“治安管理大队那边说卖了近万张票,我估计现在六七千人怎么都有,只会多不会少。”张伟告诉杜然自己的猜测,又继续问他,“那你觉得这里离观众多的那边有多远?”
“四五百米?看不出。”
“你这是什么天眼!”张伟笑了杜然一句,然后教他应该怎么判断出正确的距离,“先看面前的路牌咯,指着大门的方向写了‘前方200米’,目测和到草坪那边差不多,甚至还要远一点,所以我估计草坪离这边也就180米左右。”
“哦哟!”杜然阴阳怪气地称赞那还是伟哥厉害。
张伟让他把这话留到完成林队布置的任务后再说。
杜然轻哼一声:“完得成就有鬼了。”
张伟让他别闹情绪了,商量着要不还是从血衣下手。
“时间太紧了,我觉得不现实。”杜然确实有些发脾气的意思,“里面那些人刚才已经问过一圈了,都没看到血衣呢!”
张伟对他有些无语,杜然反倒是来了说话的兴致。
“你不是说现场有六七千人,哪里问得过来咯?还要一边问,一边注意低调保密,不能泄露案情造成恐慌,这不自相矛盾?”
“也别这么想,我认为林队的思路还是靠谱的。现场的血喷了一两米远,地上一大片,凶手作案十有八九染了血衣,既然在里面没有找到,那应该是带离了现场。”张伟耐着性子继续和他商量,“现在关键问题是,如果他穿着血衣从茶社走出来,那也太显眼了,怎么就没人注意?是不是用了什么办法?可以重点从这里想一想。”
“按照法医说的,凶器上全是血,那应该胳膊手上都是血咯!凶手一身血,茶社里外都是人,他出来怎么可能没被注意?有血衣还轮得到我们去找?早有人报警了。”杜然骂了一句“他妈的”,一肚子火。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张伟瞪了他一眼。
“伟哥,不是说我丈母娘的葬礼还没散棚,我家人在殡仪馆哭得稀里哗啦的,林队把我叫过来了我有意见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橘子洲常年演出多,治安管理大队那边任务多,锦旗、奖励和表彰也就多。平时不出事,那一个个在局里调子高得……牛逼哄哄的,几时把我们看在眼里?好咯,现在这么多人安保,保出这么个名堂,真一有事,还不是让我们来擦屁股?你看那个刘队——”杜然模仿出刘勇刚才毕恭毕敬的样子,学起刘勇的腔调来,“辛苦刑侦的兄弟们了,尽快帮忙解决……”
张伟拉下脸来,说都是同事,让他少讲两句。
“讲两句怎么了?”杜然把头扭到一边,咂了咂嘴。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话?不觉得浪费时间吗?我看你就是有意见!”张伟终于受不了他了,说他小家子气,“你有脾气我可以理解,说实话你这个情况我也不想你来,但是干这行能怎么办呢,入警誓词你当年没背过吗?什么叫‘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来都来了,要么先把事情办好,要么你干脆去跟林队请个假,回去算了?”
“好好好,不和你闹了,我们现在也总得先定个方向吧?”杜然听张伟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还是赶紧结束了牢骚,“走咯!走咯!去哪边问,你说?”
绕过一辆白色的电视台导播车,浩南被人拦了下来。
林队让浩南调查罗门说的舞台激光与昨天监控器损坏的事情,他径直来到演出区域的后台。
“不好意思!”音乐太吵,脖子上挂着证件的年轻男性工作人员扯着嗓子,伸手阻拦,“这里面是后台,观众不能进去。”
浩南从裤兜里掏出警官证表明自己的身份,凑到耳边告诉他有些事情,要进去找人。
小年轻一脸惊慌,请他在帐子外面等一下,得先进去问问。
很快,一个长发女人跟着走出来,同浩南礼貌地握手,凑近了大声说自己是音乐节演出公司的后台负责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浩南告诉她,现在有个治安问题要找昨天控制舞台激光的人,问他在不在里面。
“这边是后台,是乐队休息和准备演出的地方,灯光师和调音师都不在这边的!”女负责人大声告诉他。
浩南顺着她伸长的胳膊望去,乌压压一片观众脑袋的上方,除了两台不停移动的大摇臂摄影机,还搭有一个金属脚手架的高棚。乍看是一处星星造型的展板,上面却有几个小小的人影在操控着电脑和控制台。
她说:“今天和昨天的灯光都是请的同一位老师。他们在那个架子上面,你得去那边问问。”
浩南若有所悟。自己确实想当然了,灯光师怎么会在后台呢?灯光师需要实时看到舞台的效果,才能操控灯光的变化,所以肯定不会待在后台这种背对着舞台的地方,应该在正面视野能覆盖到整个舞台的高处。
他简短地向女人道了一声“谢谢”,便向着高棚小跑过去。
“嘿!你谁啊?”
好不容易穿过人群,浩南歇了口气之后,拉着梯子往上爬。一抬头,先看见一张垂下来的工作证,再看见一张皮包骨的瘦脸,告诉他这里不准上来。
“我是警察,有点事想问你们的灯光师。”他照例摸出警官证,对方接过去仔细看了看,偷偷笑了一下。
“有点意思啊,哥们儿!警察竟然取了个名字叫浩南,”精瘦的男人把警官证还回去,告诉他,“不过可不可以等演出结束之后再说啊?现在我师父忙着呢。”
“你师父?”
浩南看向他背后,一个穿着洋气紫色西装的寸头中年男人正在不停操作着电脑和控制台上的按钮。对讲机里传来声音,急促地喊道:“给主唱一个追光!给主唱一个追光到舞台边缘!他马上要solo了!”
浩南看向舞台,果然,一束白光跟着抱吉他的人快速前进,那人竖着吉他飞快地弹奏,大屏幕上现出镜头特写,音响里爆出密集的鼓点和一层层声浪,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是浩南第一次来音乐节现场。尽管同事罗门就在玩乐队,自己平时也用手机和电脑听些欧美老牌摇滚乐,但这是他头一回体验到这种耳膜和心肺被震到发颤的感觉。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正在演出的乐队,也从未听过他们的歌,却还是被演出的氛围所感染。此刻,他才终于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花钱来听现场——和这种感官全开的体验相比,耳机、音响传递出来的声音,确实显得太过简陋了。
“阿Sir同志?”
等他回过神来,寸头灯光师已经把控制台暂时转交给了徒弟。他们相互凑近了脑袋,扯着嗓子说话。
“你有什么问题?快点问,我好忙。”灯光师讲话有些粤语口音。
“你好,昨天的演出,那些激光,也都是你们在弄吗?”浩南直奔主题。
“怎么了?”
“昨天下午六七点左右,这沙滩公园的安防监控器突然坏了好几个,我们有同事说你的舞台激光能烧毁摄像头里面的什么传感器,你觉得有可能吗?”
“没理由啦。”灯光师几乎没有思考,直接否定了罗门之前提出的假设。
“为什么?”浩南认为他否定得太直接了,显得有些敷衍。
“有时观众站在舞台很前拿单反拍照,离光源好近,有烧到CMOS的情况啦,但监控器里边的CMOS传感器,最多指甲大小。”灯光师捏着小拇指指甲给浩南看,“你说离舞台近,烧坏了一个我信,你们的监控器,十来米的间隔距离,一下子被激光烧坏了好几个?想都不用想,没理由的啦。”
浩南追问,具体是怎么没可能。
“我跟你讲,舞台激光动态效果要做得靓,好复杂的。我们都是成套成套动作提前编好程序,角度和运动轨迹都是固定的。用的时候直接让它按照程序走。舞台激光一个点有多大啊?随便划几下就正好照到那么多指甲盖大小的CMOS上?同你拔出手枪乱射,全都射中蚊子差不多!你觉得有可能吗?又不是周星驰搞笑电影。”
浩南锁住眉头,思考着灯光师给出的解释。
“这些程序都是你亲自编的?我对你们的技术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如果有人事先计算好了激光的发射角度,就是为了烧毁监控去的呢?就像我们射击的时候,会事先瞄准一样,写一套正好包含所有监控器位置的运动轨迹在你这设备里面,然后再运行一遍?”
“没理由啦!这场音乐节激光,全部我做的。”
灯光师吸了一口气,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你讲的这种,发梦啦!刚刚同你解释过,CMOS和激光光点面积都好小,距离远一点,误差就大好多。这个你懂射击瞄准,肯定懂啦。为什么靶子越远就越打不准呢?舞台灯光讲究的是整体光效靓嘛,光源的安装位置,不会控制到那么小误差啦!几厘?几毫?根本没人可以事先把舞台激光算得这么准。以为是玩激光武器?全国的舞台灯光师,你放心吧,没人做得到这样子啦!如果有,我都去拜师了。”
“哎呀!我专业玩光的,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的啦!你们的监控器坏了,肯定和我的激光无关的。”看浩南的表情仍有疑虑,灯光师继续向他做各种解释。
“阿Sir啊,你讲的这些,什么拿激光照监控器,就算我有条件慢慢在现场调角度,一点点人工瞄准,但是昨天下午六七点,演出都已经开始好久了!好鬼多人,我在这么多人眼皮底下,拿一束激光四处飘,专门找你们的监控器射击,你以为观众瞎吗?
“你看我们这个棚面向舞台,视野好小,后边都看不到,怎么瞄?再讲啦,舞台激光灯又不是激光武器,功率又不大,远一点能量就好差了,绝对照不坏那么远的CMOS。
“你们监控器,里面我不懂,但是我猜,至少不同监控的视角要看好多地方是吧?没可能所有镜头都正好对住激光灯的方向,对不对?那我问你,激光怎么可能射到传感器呢?不用想啦,没理由的,都不用想……”
浩南皱成“川”字的眉心瞬间放松,嘴缓缓吐出一个“是哦”。
他的说法确实没错,激光的轨迹再怎么变化,也都是从舞台方向发射出来的,而这么多监控的摄像头不可能全部指着舞台的方向。这么简单的道理,竟然没有早些想到。罗门在提出舞台激光这个假设的时候,明明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哪里不对,绕这么大一圈,才被灯光师点醒,浩南一拍脑袋,感到是自己糊涂了。
可是如果不是激光,那么多监控,又是怎么被破坏的?
“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能重拾彼此的欣赏。我们拥抱舞蹈歌唱中度过动人美丽时光……”[5]
欢呼过后,舞台短暂地安静下来,一首歌结束了。
浩南望向下面黑压压一片不停攒动的脑袋凝神,把眉间的“川”字又挤了出来。
几棵笔直的水杉下,有人在折叠地垫,把没卖完的小玩意收拾进背包,准备离去。也有两三个摊主或站或坐,举着清冷的LED照明灯,仍在继续少有人问津的生意。
这些摆摊的并不是街边卖十元五双袜子或者手机壳膜的小摊小贩,而是音乐节主办方以“文艺集市”为名请来的创意店主。他们卖头饰丝巾、手工艺品、绝版CD、自印诗集等等一些契合音乐节主题的小东西,挺受年轻人的喜爱。
玩乐队的同事罗门离开茶社前,张伟向他了解了音乐节大致的演出流程。每天一般下午两点左右观众开始验票进场,按照名气大小,共有十支乐队轮番上台。
当时杜然还顺嘴问了他的乐队是第几个表演的,罗门回答说是第二个。
“我们三四点就演完了,天都还没黑呢。”
“哇,排这么前!你现在乐队玩得挺出名啊!”杜然很是吃惊。
结果罗门有些尴尬地向杜然解释,一般音乐节,名气越大的乐队,表演时间都是越靠后的。“最后的乐队”一般是最具知名度的,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观众人数也最多。而越早表演,越带有暖场性质,更多的是一些像他们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本土小乐队。没什么粉丝,观众常常少得可怜。
“白天太晒,灯光、舞台这些都做不出太好的效果,没什么氛围,观众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舞台这边。”
罗门说,为了弥补大牌上场之前这些小乐队演出可能吸引力不足的问题,音乐节的主办方通常还会在场地内设置一些其他的项目供观众消遣游玩。聚集在杉树下小片草地上的“文艺集市”正是星城音乐节的特色项目,效果挺好。
下午,对暖场乐队没感觉的观众会喜欢来这边逛逛,挑选一些各自想买的文艺商品。从5点开始,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的表演者登场,人数的天平会慢慢向着舞台那边倾斜。直到7点过后,天色慢慢暗下,重量级乐队陆续露面,观众们会为了抢占更靠近偶像的位置,向着灿烂夺目的舞台涌去,市集这边才开始冷清下来。
“美女,是要收摊了吗?”
杜然看见一个拿着画笔和调色盘的女孩,扯了扯张伟的Polo衫衣角,开始和她搭话。
“没有啊,你们要画吗?”
张伟低头才发现杜然的拉扯在暗示他什么,这女孩的亚麻色围裙上,是一大片暗红色的污渍。
“你是画……那种肖像油画的吗?你的画布呢?什么都没有怎么画呀?”
女孩子看他们一本正经绷着的脸,察觉到了什么。
她问:“你们不是来音乐节玩的吧?”
“我们是警察,在进行一些安保方面的排查,请你积极配合。”杜然直截了当。
“哦,好。我是来画油彩的,不卖肖像画。”
“画油彩?”
女孩把画笔倒过来,指着自己脸上的爱心给他们看:“就是在脸上、胳膊上、手背上画些红红绿绿五颜六色的啊,你们没看到别人有吗?下午我给好多人都画过了。”
“你专门做这个?这种叫什么?人体彩绘?”
女孩扑哧一笑:“不是啊,我本来是个文身师,太平街那边巷子里开文身店的。前两年这边的活动策划找到我,拿其他音乐节的照片给我看,问我会不会画这种很多音乐节都有的脸部油彩。我觉得简单,就来画咯。他们看我画得不错,这两年都找了我来画的。”
“可以看看你的围裙吗?”
“哦,可以呀。”女孩俯身看了下自己的围裙,“你们不会以为这是血吧?这是颜料啦。”
张伟没作声,上前稍微看了一下,确实是颜料,凝固的深红色的颜料。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女孩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警惕起来。
“你这是怎么弄的?”杜然不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追问。
“下午帮一对父女画,小女孩太调皮了坐不住,乱动手脚打翻了我的调色盘,弄了一身。”
“我看你这边怎么好像都是红颜料?”
“很多人都喜欢画红的啊,我红颜料就用得多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红色呢?”
“那我不清楚……色彩心理学吧。这种年轻人出来玩的热闹聚会,就喜欢激情奔放一点的颜色呗。”
“这么说来,刚刚确实看到有人脸上画了一些东西,星星月亮之类的,也有很抽象的,涂鸦的那种,是吧?”张伟问。
“是的,也有人就让我随便涂的,说越乱七八糟越好。我每次问他们会不会太夸张,他们都说越乱才越摇滚。”女孩说。
张伟撇撇嘴,好像觉得这种想法挺肤浅。
“有没有人找你画过那种——”杜然轻轻把五指张开,想把自己的问题比画得更具体一些,“泼溅效果的红色油彩?”
张伟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也知道他这么问的原因,但女孩也不是傻瓜。杜然越问越多,她就越紧张,慢吞吞地吐出一句:“好像没有。”
“这里还有别人画油彩吗?”
“应该没有。”女孩又忍不住急急地问了一遍,“警察叔叔,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呀?”
“你别吓着人家了……”张伟把杜然拉到一边。
他试图安抚女孩的情绪,告诉她也没什么大事,又搬出他那套惯用的话术,“保密的义务”啦、“案情的需要”啦、“警民配合对社会治安的必要性”啦,让女孩答应下来不去和别人声张刚才的谈话,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感谢你的积极配合!如果有必要会再联系你。多提醒一句,这种场所人多事杂,女孩子千万注意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遇到什么情况,随时联系。也别太担心、太紧张啊,没事的,有我们在呢。”
张伟虽然大龄未婚,但挺讨女孩子喜欢,杜然每次问他诀窍,他都说没有诀窍。在女孩的目光中,两人晃荡的身影慢慢走远。
“你刚才那么问,是不是在想着,凶手根本没有刻意掩藏自己身上的血渍和血衣?假如他是画了那种与血色相近的油彩进茶社,佯装上厕所然后上楼杀人,没准别人会把作案之后的血迹当油彩的一部分?”
“伟哥你懂我。我确实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之前太紧绷,走到了误区?”
“什么误区?”
“一直认为这么多人在场,凶手一定会特别仔细地处理身上的血衣和血渍后才敢出来,但很可能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人多,谁也不会特别在意谁。”他拿手指在自己脸上比画,“如果凶手提前做了这种伪装,本来就是打算蒙混过关呢?”
“可是那个油彩啊……能做到几分逼真先不说,即便是可以很好地掩盖作案后的血迹,应该也没人会这样搞吧?弄那样的油彩在身上,越逼真就越跟杀了人似的,作案之前就很招摇啊,回头率绝对高,不可能不被注意到。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想法不太成立。”
“我刚才那么问她,只是一个随便冒出来的灵感。我现在不是想和你讨论油彩本身,而是想到‘油彩都能简单伪装’之后打开的思路。我们真的不要把血衣的问题想得太复杂、太精密了,自己钻进牛角尖里去。”
“啧,看来骂你一下还是有效果嘛,开始有灵感了?”张伟笑了笑,拍了拍杜然肩膀。
“别闹咯,说正经的。我们办了这么多案子,遇到过几次真正的高智商犯罪?那些都是小说和电视剧里面骗人的。杀人犯嘛,本身就是亡命之徒了,他们有几个不是看运气的?运气好,碰巧没被人发现,万事大吉。运气不好,被人发现就逃,逃得掉是本事,逃不掉烂命一条,你说是不?我讲个最简单的办法,没准杀手就是穿了件长袖的外套,杀人的时候先把外套脱了,杀完再穿上,盖住了血衣和身上的血渍,然后逃走了。现场这么多人,谁会盯着个陌生人看那么仔细?”
“这么热的秋老虎天,凶手穿长袖外套来看演出,很奇怪吧?”
张伟提问时开始带着浅浅的笑意,他感觉工作正在回到正轨。两人通常的合作也是这样子,师弟杜然负责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自己则擅长质疑和补充。
杜然伸出手指给他看:“那些环卫工人,不都穿着长袖的工作服吗?”
“那衣服也很薄啊,我感觉血迹会渗出来的。”
“渗出来不要紧,深色的衣服就看不出来了。”
“哪里有人穿深色的长袖衣服?”张伟眯起眼睛四下顾望。
“你瞎呀?那些搞安保的、来给治安管理大队值班的兄弟,还有我们刘队啊,不都穿着深色的制服?”
张伟看着杜然的脸,他的表情不像是调侃。
“这种话,可别瞎说……”嘴上这样说,他也抱着胳膊思索了起来,“不过这样的话,凶手是不是应该在包厢里面换好了衣服,再出来的?”
“那肯定啊,毕竟出了门,楼梯过道上就是厕所,不在包厢里换,很容易被人看到的。”
“那进门之前呢?我们刚进现场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个事情被忽略了,”张伟挠了挠小臂,看着杜然的脸,“刚刚你一说换衣服,我灵光一闪,想到了那个包厢。”
“包厢怎么了?”
“你说……”张伟的语气有些迟疑,“那个黎总被害之前,一个人在包厢里面喝茶,这时候突然进来了个人,把他从身后捂住嘴,一刀割喉了,是吧?”
“法医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这回轮到杜然挠脑袋了。
“开门肯定有响动的,一个陌生人进来靠近他,你说他不喊叫也不躲避和挣扎?还背对着人家被杀了,不太可能吧?”
“我懂你的意思了!”杜然惊呼,“林队一开始从手法专业与否上面判断现场,觉得一定是惯犯或者职业杀手干的。但其实还不只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哦,如果他当时是正常清醒的状态,包厢现场都不可能是那么平静的!”
“没错,且不说目前法医没发现致昏迷药物的迹象或创伤,如果被害人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杀手也没必要像法医说的,那么用力地捂住他的嘴。”
“伟哥,你讲的有道理。那个黎总当时在包厢里,凶犯进门,他应该就能发现。既然他发现了凶犯,凶犯就很难从他背后一刀割喉,还没有争斗的痕迹。那个死法,应该是黎总知道凶手进了包厢,但又对他没有提防?你是想说……”杜然挑明了张伟的结论,“他俩应该是熟人?”
舞台两侧的LED大屏幕上,镜头对准了一位在撩垂发的女孩。
她的脸已经被汗水浸湿,显出兴奋的红晕,是那种具备电影镜头感的漂亮。发现自己被摄像师拍到了,她赶忙害羞地抬起胳膊捂住嘴笑起来,更动人了。
“等等,我问一下!”浩南抓住正要转身的灯光师。
他指着一直悬在空中,不时转动的大摇臂摄影机黑影:“这个舞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直播的吧?用那两台摄影机拍的?”
灯光师摸了摸自己被抓皱的西服,说当然是的。
“也是你控制?”
灯光师指着徒弟身边操作另一处工作台上电脑的人,说LED屏幕上的画面是由他来决定的。
“你这些直播的视频,储存了吗?”浩南冲他喊了一句。
“我没有,别找我。”VJ[6]盯着软件界面的脸,冷漠得像和谁吵架赌气一样,眼睛和手都在忙碌着,全神贯注。
“直播只一条信号线给到这边,”好在灯光师有耐心,替他解答了问题,“VJ用的时候切一下。但是指导摄影师拍摄的导播啊这些,又是其他人做。有没有储存,你去问他们啦。有时主办方想以后剪出些演出视频,就会储存。你头先问完激光,又问这些做什么?”
浩南很急,问他导播在哪里。
灯光师说这次主办方请的是湖南电视台的专业团队,应该在后台那边,有一辆白色的导播车。
浩南谢过灯光师转身而去,穿过拥挤的人群,再次回到后台附近,那辆导播车外。
他气喘吁吁、浑身是汗,撑着膝盖喘了几口气,拉着扶手登进车厢。里面三人一齐转过头来,看着他起伏剧烈的胸腔。
“打扰了,我公安局的!想问一下,你们外面那两个动来动去的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有没有储存?”
“别吓人好吧,都忙着呢!”戴着大耳机、挂着工作证的胖子有些娘娘腔,翻了个白眼,继续转身去工作。
“二号机,绕过去,绕过去!拉近了给鼓手一个特写,然后依次是贝斯、键盘和吉他,最后给主唱!他要唱了!动起来!快!快!快!”另一个胖子拿着对讲机大吼道,“你是猪吗?‘动起来’听不明白?都开始唱了你还在拍你妈的鼓手啊!”
另外一人是个看上去年轻很多的女孩子,她拧开矿泉水递给那个骂人的胖子,看起来像个实习生。
她小心翼翼地说,要不还是等他们工作完了再来问吧,这会儿确实挺忙的。
浩南说不行,很急,视频有存储的话,他现在就要看。
“那就没有存!”浩南越急,坐着的胖子就越不耐烦。
“你们他妈的是要逗霸不咯[7]!”
浩南怒从中来,大吼了一声,刚刚还在骂人的胖子突然安静下来,吞了吞口水。
又是这样的结果,难免让人感到沮丧。
浩南最近一直在训练自己克制情绪,用更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干这一行,每到关键时刻,温和的方式都效率低下、于事无补。同事们都喜欢戏谑着称赞他工作起来“霸气”,但他从没和别人提起过,自己更羡慕罗门那种谦和的性格。
“您到底要看什么?”给浩南开机后,实习生小姑娘站得远,有点怕他。
浩南一直按着快进,清了清嗓问实习生小姑娘,昨天下午6点左右开始,有没有拍观众的摄像机拍到过沙滩公园西边一点的监控器。
小姑娘有些羞怯地问他说的西边是哪一边。
“正对舞台观众的左边,一直往南的方向。那边好像有些摆摊的,然后有个茶室。有拍到路边监控器白色柱子的,都可以。”
实习生女孩说她来找找看,然后动动鼠标,关掉浩南打开的名为“2014082317_03.mp4”的视频文件,打开“2014082318_02.mp4”,拖动了几下时间轴,问他是不是这个。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汗衫、摇动着伟人头像下写有“摇滚湘军”红色旗帜的文身男,正站在离舞台最近的那处监控器旁边三米左右的地方,狂喊“牛逼”,为台上的乐队声援打气。舞台摄像机在他身边停留了几秒,因为一直在运动,监控器在画面中有些模糊,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时候监控器四周白色的LED补光灯还亮着,浩南看在眼里。
他问还有别的没有。
实习生女孩又拖了几下时间轴,无非就是一些音乐节观众的表情特写,偶尔扫到了几处有摄像头的,但看不出什么特别的。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实习生女孩小声呢喃了一句,点开文件夹里的“2014082317_02.mp4”,迅速地拖了几下时间轴。
画面中白色的监控器柱子,还是刚才第一次看见的那根,但柱子底下站着的人,却显得和音乐节格格不入。那是一位穿着职业西装、梳着偏分头的中年男人。他伸直了手臂,露出白色的衬衣衣袖,举着一个灰色的大喇叭,尽可能地用喇叭贴近监控器,像是在为监控器“播放”着什么。而监控器镜头周围的LED补光灯,在忽明忽暗地闪烁了几下之后,竟然熄灭了。
这一幕简直像魔法,浩南不敢相信,露出惊愕的表情。画面里的中年男人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拍到了,也一脸惊愕,然后尴尬地笑起来,朝着这边挥了挥手。
“特搞笑,这个人穿着西装,举着个大喇叭给监控器听,不知道他在干吗……摄影师可能觉得他在搞行为艺术吧,就让他‘上墙’了。我还想着提醒高老师之后剪进现场回顾片里呢,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很显然,这不是什么行为艺术,但这喇叭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破坏监控器?浩南一头雾水。
“你们这些视频我现在要征用了,昨天和今天,所有机位的全部文件都要,等之后办完事情再还给你们。”
他一边吩咐现场电视台导播车里的三人,一边拨通了林立莲的电话。
“林队,是我。破坏监控器的关键线索找到了,看上去不是激光,是一种别的什么工具吧,像是那种小摊小贩用的扩音器。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也许是超声波之类的?对,是个男的,个子不高,穿灰色西装……人是从舞台这边的摄像机里找到的。
“等下市局那边,视频侦查大队会来人吗?我现在要了电视台的视频存档,监控没有了,他们拍了挺多的,虽然集中在舞台这一边,但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其他有价值的影像……这个人的身份识别也得辛苦视侦他们了。
“对,我感觉和咱们的案子关联性很强……”
他用肩膀夹着手机,下意识地继续播放舞台摄像机拍到的画面,突然,一阵电流从键盘和手指间流过,让他全身的汗毛直竖。这男人的长相当然谈不上多面熟,但好像实在又没有那么陌生,仔细看看他灰色西装肩部有些过于紧凑的剪裁,血渍晕染的画面便开始在脑海中慢慢浮现。
“林队!等等,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应该就是死——”浩南吞了吞口水,幸好没有鲁莽,换成名字说出口,“黎万钟啊。”
“欸!我昨天看到过这个人咧,也认得他那个喇叭,”刚才还在大声骂人的胖子冷不丁出现在浩南身后,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昨天下午我在车外抽烟,正好看到他拿着那个喇叭,从后台走出来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用夸克网盘分享了「刹那_郭沛文.txt」,点击链接即可保存。打开「夸克APP」,无需下载在线播放视频,畅享原画5倍速,支持电视投屏。
链接:https://pan.quark.cn/s/8dc8e1a090d5
提取码:xxAJ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刹那_郭沛文.txt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FRLWPsC36qdFKf2RKDPWA?pwd=u2tb 提取码: u2tb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1的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链接:https://caiyun.139.com/m/i?2iN0a0bFue821
提取码:eba7
复制内容打开移动云盘PC客户端,操作更方便哦
为促进文化交流,本站整理收录的小说资源均源自网络公开信息,并遵循以下原则:
1、公益共享:本站为非盈利性文学索引平台,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收费性质的阅读与下载服务;
2、版权归属:所有作品著作权及衍生权利均归属原作者/版权方,本站不主张任何内容所有权;
3、侵权响应:如权利人认为本站展示内容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把该作品相关材料私信至站主或者发件到邮箱。经过核实后,本站将会在48小时内永久下架相关作品。邮箱tegw202@gmail.com
4、用户义务: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利用本站资源进行商业牟利、盗版传播等违法行为。
5、我们始终尊重原创精神,倡导用户通过正版渠道支持创作者。如对版权声明存疑,请联系我们进一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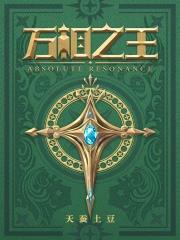


![《[最新]豪乳老师刘艳》连载 (1-9部35章+番外同人) 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uploads/2025/03/20250408195915145-《豪乳老师刘艳》1-8部120章-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jpg)















![表情[xiaoku]-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xiaoku.gif) 三十多兆的小说。。。
三十多兆的小说。。。![表情[tuosai]-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tuosai.gif)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