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重生/东方玄幻/朝堂权谋/后宫/轻松/无敌流/快节奏/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在拥有足够自保能力后
竭尽全力
争取事业、爱情双丰收
畅享人生
逍遥快乐
暂定一个小目标——先活上一千年!
标签:热血 腹黑
楔子一 和尚的哀鸣
那一日,江山小雪。
北溟浩瀚,鲸龙潜伏,一座座太古冰山漂浮银蓝色浪涛之上,寒风呼啸,卷起漫天玉龙碎鳞,三条舟船逆风而行,如箭矢穿波跨浪,穿行座座冰山,一路径直向北。
一条舟船长不过十尺,船体尽成青色,乃一根万年古松树干整体抠成。
两个眉清目秀的小道童驾驭木舟,一名青年道人盘坐船头,手持玉箫,吹着一首淡淡雅雅的曲子,飘逸出尘宛如仙人。
一条舟船长达百丈,船体为青铜铸就,前后三重船楼,通体雕刻无数鬼神图案,威严而狰狞霸道。
舟船甲板上,矗立着数百身披重甲魁梧大汉,一个个生得威武霸道,周身杀气腾腾。
一名比寻常人高出将近两尺的壮汉裹着一裘白虎踏云战袍,手持两丈四尺白虎戟,面带冷笑左顾右盼,顾盼之间眼眸中寒光四射,目光宛如实质,端的气势逼人。
一条舟船长有一丈六尺,船体呈淡金色,却是一根根晶莹剔透宛如金色琉璃的骨骼拼凑而成。
这条舟船并无人驾驭,船上唯有一名身穿雪白长袍的俊俏僧人盘坐。
头皮刮得溜光,头顶有九颗淡金色戒疤的僧人面带微笑,双手捧着一卷青色树叶钉成的经卷,慢吞吞一个字一个字的诵读着。
青年道人箫声响起,曲调婉转波折间,舟船下方隐隐就有云气晃荡,舟船的速度就一点点不断提升。
俊俏僧人诵读经文时,每一字、每一词出口,骨舟光芒就微微闪烁,每次闪烁,骨舟都骤然向前奔驰数百丈。
那壮汉所乘青铜巨舟却无任何神异表现,只是道人、僧人所乘坐舟船还要绕过一座座巨型冰山蜿蜒前行,他所在的巨舟却是蛮横无比直接撞过。
无论百多尺的小冰山,还是千多丈的大家伙,这条巨舟速度丝毫不减径直穿过。
从高空俯瞰,三条舟船各有神通,大致上是齐头并进,谁也甩不下哪个。
船行不知数万里,绕过一片盘桓洋面如长城的冰崖,前方天色豁然敞亮。
风不动,雪消停。
茫茫洋面上白雾升腾,刺骨寒气凭空萌发,在洋面上凝成了一朵朵巴掌大小,白色的冰晶莲花。
三条舟船放慢了速度,缓缓的从洋面上划过。
船体撞击洋面上凝聚的冰晶白莲,发出细微的‘叮叮’声响。
这一片海域,天、水尽成一片银蓝,高空不见云彩,一轮大日懒懒悬挂在极远极远的天边,阳光被空气中无数细碎的冰晶折射了无数次,一轮轮七彩虹霓宛如海市蜃楼,在众人身边盘旋闪现。
向前再行数千里,一只巨掌从海水下突兀探出。
此处海水极其清澈,无鱼,无虾,无鲸、蛟、鳌、龟之属,就连一片海藻都踪影全无。
透过海水,可见一尊极大、极大的道人石雕静静的盘坐在深不可测的海水中。
这石道人,也不知通体有多么大小。
单单他探出海面的那一只手掌,手掌心的面积,就有数里方圆。
道人掌心,托着一座通体五色的大山。
大山之巅,站着一尊四面八臂、面容狰狞的百丈巨人。
这巨人身躯残破,通体密布无数大大小小的透明窟窿,透过那窄窄的、锋利的透明伤口,可见体内五彩晶莹宛如琉璃宝珠的五脏六腑。
岁月不知过去了多久,这巨人体内,依旧有黑烟、黑炎不断冒出,透过一个个伤口,宛如蒸包子的蒸笼一样,腾腾的向四周散发。
在这巨人面朝北面的那张面孔上,他嘴里一根莲茎蜿蜒生出,一路向上生长,长到了他头顶上,绽放开了一朵方圆有十几丈的红莲。
三条舟船在石道人探出海面的手掌附近停下。
道人、壮汉、和尚,三人同时向那石道人的手掌、手掌上的巨汉、巨汉嘴里叼着的那一朵莲花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腾空而起,轻轻巧巧的落在了那一朵盛开的红莲上。
千瓣红莲,中间莲台方圆不过三丈,一名生得姿容绝美、端庄神圣的女子,静静的盘坐在莲台正中。
她发髻高挽,一裘白裙,通体披挂着无数璎珞宝珠,左手托一净水钵盂,右手结不动印,轻轻向前点出。
女子双眼紧闭,暴露在外的、白皙润泽如象牙的皮肤上,密密麻麻尽是裂痕。
一如一尊被不小心打碎的白瓷宝瓶,却因为某种奇异的力量,依旧紧紧的粘合在一起。
她的右手不动印前,一缕淡淡的紫色光气若隐若现。
光气长不过三寸,比头发丝还要细千百倍。
一股可怕的凌厉锋芒,不断从那光气中缓缓渗出,一点点的侵蚀着女子的躯体。
道人、壮汉、和尚飞身上了莲台,他们凝气、屏息,战战兢兢的看向女子指尖的那一缕紫色光气。
‘啵’的一声脆响。
紫色光气悄然崩碎。
女子通体披挂的璎珞宝珠同时‘咔咔’碎裂,各色碎片‘噼里啪啦’的洒了一地都是。
‘咔嚓’一声,下方支撑这一座红莲的四面八臂巨汉的躯体,骤然裂开了七八条从头到脚、几乎将整个身躯撕裂的巨大裂口。
伴随着刺耳的碎裂声,下方的石道人通体,也不断出现一条条大大小小的裂痕。
道人微笑,用力挥动了一下手中玉箫:“挡住了!”
壮汉狂笑,他原地跳起,在空中翻了三个跟头:“哈,挡住了!”
僧人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向那浑身密布无数裂痕的女子顶礼膜拜了下去:“善哉,挡住了。”
道人微笑,摇头,向那盘坐在莲台上的女子稽首一礼,然后脚踏清风,飘然回到船头:“清风,明月,速速归去。我等道途,成矣!”
那大汉带着一道狂风从天而降,重重的砸在青铜巨舟的船头。
他手舞足蹈的大吼:“速速归去,速速归去。嘻,牛鼻子,死秃驴,这道途,还是要争一争。”
数百彪猛大汉齐声狂笑,笑声中,青铜巨舟急速调头,带起一道狂飙急速远去。
和尚站在莲台上,俯瞰着两条远去的舟船,轻轻的摇了摇头:“你等且去,却也不急一时。我教先贤骸骨,自当恭迎回山则个。”
和尚微笑,摇头,然后再次向那女子顶礼膜拜,喃喃念诵一篇超度经文。
两条舟船已然远去,视野中再不见丝毫踪影。
和尚从袖子里取出一块金色锦缎,又朝着女子拜了又拜,毕恭毕敬的走到她身前,正要捧起她的身躯,一声轻笑突然从他身后传来。
‘噗嗤’一笑,声音甜美而柔媚,端的是销魂蚀骨。
和尚瞳孔骤然一缩,就听到身后一声娇滴滴的呼喊声传来:“相公,我们配对耍子来?”
漫天七彩虹霓缓缓旋转。
洋面上,朵朵冰晶白莲轻轻对撞。
和尚一声凄厉的惨嚎响彻云霄,然后再也没有半点儿声息。
巨大无比的尸道人、身躯魁伟的四面八臂巨汉、莲台上的女子,同时在和尚的惨嗥声中崩塌、瓦解,坠入深渊。
微风吹过,寒气萌发,洋面上朵朵白莲凝聚。
银蓝色洋面上,映出了一双艳红色的绣花鞋。
楔子二 学正的哀鸣
江山大雪,雪笼镐京。
万古名城镐京,乃十八朝之古都,世间城池,尊贵莫过于它,风流自然也莫过于它。
镐京城内,纵横各四十九条人工城内运河,将四四方方的镐京城,分成了两千多个大小不一、同样四四方方的坊市。
镐京宫城,当今天子之居所,就在城北四条运河围绕之中。
距离宫城最近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大坊,这四大坊内,尽是大院朱门,里面住的,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开国元勋。
民安坊,最西北角,距离宫城最近的区域,一座老大的宅院被青松翠柏环绕,饶是寒冬腊月遍地雪白,整个占地上千亩的宅院依旧绿意葱茏,朱门、碧瓦、白墙、绿树,通体散发出一股子古老尊贵的味儿。
这是莱国公府,大胤武朝开国武勋之家。
近些年来,莱国公府族中儿孙多不成器,略有些走下坡路。但,老祖宗豁出去性命打下的家底子放在那里,纵然稍有破落,那顶级豪门的气派,却是丝毫不坠。
莱国公府东北角,祖宗祠堂的隔壁,圈出了老大一块四四方方的地盘。
这里建了几座四平八稳的大瓦房,一律是水磨青砖铺地,雪白的细纸糊墙,天棚是用带香味的细木条拼织而成,用木条的天然条纹,拼出了偌大一副鲤鱼跳龙门的图像。
大瓦房四壁,都有澄透的大水晶窗,天光透过大块水晶照了进来,屋子里丝毫不显昏暗。
偌大的房间下面,烧了火龙,大冬天的,屋子里依旧是热气腾腾暖和得紧。
这里,就是莱国公府的族学。
莱国公府,每年在族学里洒下大把银子,聘了一些颇有名声的先生,但凡一应莱国公府的直系旁支,乃至亲眷亲友,所有子弟年满五岁后,都可来族学读书。
一间大瓦房中,一张张书案摆放得整整齐齐,书案上堆积着各色书本,放着文房四宝。
书案后,一张张凳子上,端坐着莱国公一脉,年龄从十四岁到十八岁的一众年轻族人。教室宽敞,空间极大,莱国公一脉适龄的年轻族人,总数将近两百,悉数在这教室里坐着。
卢仚满头长发扎了个大马尾,穿着一件青布的对襟大棉褂子,双手揣在松松垮垮的袖子里,坐在房间的最后一排角落里,透过水晶窗,看着对面教室屋檐上几只蹦跶来去的麻雀。
已然腊月,临近小年,族学一年的课程算是到了头,今日之后,就是长达一月的冬假。
两日前,族学组织了年底的考评,今日正是出成绩的日子。
教室的最前面几排,那些个出身莱国公府旁系,还有几分上进之心的小子,正紧张兮兮的看着前方讲台后的族学学正。
教室的中间位置,十几个身穿绫罗绸缎,身边有小幺儿伺候着的直系公子,正犹如一摊猪肉一样瘫在座位上,绞尽脑汁的琢磨着稍后去哪里、找哪个、做什么有趣的消遣。
教室的最后几排,也就是和卢仚比邻的那几排位置上,一些同样出身旁系,但是家中颇有几分财力、势力的小子,连同一群来族学蹭读书的亲友子弟们,一个个嬉皮笑脸的做着鬼脸,用只有他们自己知晓的暗号交流着。
偶尔,可以听到他们的几声低声笑语。
比如说,‘小桃红的胸脯’、‘小柳绿的粉臀’、‘某位嬷嬷好腰力’、‘哪位大茶壶养得好大龟’等等。
端坐在讲台上的族学学正,乃是莱国公府的近支族人,年近四十的卢俊。
十年前,卢俊被莱国公府举了孝廉,得了官身,很是气派过一段日子。但是好景不长,在任上有了巨大的钱粮亏空,却不知那公库钱粮究竟去了哪里,自己又没有力量填补窟窿,一朝事发,差点儿就丢了脑袋。
亏着莱国公府的关系,卢俊倒是没有被定罪,但是官职却是丢了。
莱国公府免了卢俊的罪,却不会替他填窟窿。
而当今天子,却是一个极看重钱财、极会经营敛财的奇葩。
卢俊身上背着巨大的钱粮烂账,除非他补齐了窟窿,否则终身复起无望。
所幸卢俊在莱国公府中,和几个正房直系的老爷有些交情,他也有几分文章华彩,也就委委屈屈的进了族学,承担起为莱国公府教育子孙、培养人才的重任。
生得颇有几分英俊清秀,两侧鬓角略显花白的卢俊也懒得管下面那些胡闹腾的小子。
国公府的直系公子们,他不敢管。
那些不成器的旁系子孙和外来户,他懒得管。
前面这几排坐着的,还有几分上进之心的小子,不需要他管。
懒懒散散的吐了一口气,端起小紫砂茶壶抿了一口老白茶,卢俊慢悠悠的从讲台下面,抽出了一个水牛皮制成的书囊,取了厚厚的一叠考卷出来。
“今年年试,成绩大体,和往年相仿。”
“尔等,切要铭记先祖富贵得来不易,需要勤勉读书,切不要堕了泾阳卢氏莱国公府一脉的赫赫威名。”
“哪,卢逊,上上。”
“哪,卢谦,上中。”
“哪,卢慎,上下。”
卢俊慢悠悠念出族学一众小子的年考成绩,那些小子无论直系、旁系、外来户,一个个走上前来,接过卢俊手中考卷,或者喜笑颜开、或者嬉皮笑脸、或者愁眉苦脸、或者混无所谓的回到座位。
卢俊一个一个名字念着,到了最后,他抖了抖手中最后一张卷子,换了一张嘴脸:“卢仚,下下。比起前两年,你是没有丝毫进展。看看你最后一篇最紧要的道论,你又是答非所问,一派胡言。”
卢俊用力敲了敲讲台,声色俱厉的指着面无表情的卢仚呵斥道:“你前年如此,去年也是如此,今年还是如此。你这般下去,可对得起族里每月补贴的银两、米粮么?”
卢俊盯着缓缓站起身来的卢仚,厉声道:“这世道,文教弟子最是尊贵,读书做学问,才是真正的光明前途。这学问上的勾当,其他尽是基础,唯有道论才是青云大道。”
“任凭你生得油头粉面,一副好皮囊,做不出好的道论来。嚇!”
卢俊将手中卷子,轻飘飘的往前一丢,任凭其落在了地上。
他指着卢仚,语气越发激烈的大声训斥:“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年年不见长进,可见你是个废物种子,只会给泾阳卢氏丢脸的腌臜废物。”
卢俊的骂声越来越激烈,口水星子喷出了老远。
卢仚轻咳一声,缓步上前。
课堂中骤然静了一静。
无论是公府的公子,还是那些远亲近亲,所有人都抬起头,看着身高近九尺,比寻常人魁梧、精神许多的卢仚。
卢仚捡起了地上的卷子,将其卷成了一个圆筒,好似握着一根棍棒一般,轻轻的敲击着自己的大腿。
他带着笑,不断的向卢俊点头:“先生责怪的是。”
卢俊不为卢仚的笑容所动,他的训斥越发的尖酸,刻薄,甚至是有点恶毒了。
“以我看来,你竟是不用读书了。”
“你若是舍不得族学里每月发放的银钱、粮食,你干脆奏明了大老爷,出去做点活计谋生,岂不是比在这里虚度时光来得好?”
“你留在族学里,不仅仅是自己丢人,竟是连卢氏族学都被你牵连,受人嘲笑了!”
“偌大的镐京,这么多大家大户,哪家族学,有你这般连续四年,都是下下考评的蠢货?”
“因为你,我出去和同年们饮酒,竟都是丢脸的了。”
“好在你阿爷死得早,你爹或许也已经死了,不然见你这般模样,岂不是生生被你气死?”
卢仚目光清幽如寒冰,面带微笑,静静的向卢俊稽首行礼,转身走回了自己座位上。
见到卢仚这等模样,卢俊的训斥更是犹如江水般滔滔不绝,差点就是破口大骂起来。
族学里,那些卢氏嫡系的公子哥,还有那些顽劣的旁支、外戚们,一个个指着卢仚‘嘻嘻哈哈’,尽情的配合着卢俊取笑他。
当天夜里,莱国公府族学的一应大小学生,凑了一笔银钱,在民安坊东面,隔了一条城内运河的安乐坊,最大的一栋酒庄‘和风细雨楼’中,办年底谢师宴,请族学的一众先生,以及学正卢俊和几位族中学监大吃了一顿。
酒宴未完,一如前两年,卢仚推辞不胜酒力,悄然离席。
酒宴毕,卢俊和一众先生呼朋唤友,又跑去和风细雨安乐楼附近的明月阁好生戏耍了一通。
深夜时分,喝得酩酊大醉的卢俊离席,拒绝了身边的秀女搀扶,摇摇晃晃的,径直一人去外面更衣。
骤然间一声惨嚎冲天而起,卢俊的哭喊声响彻明月阁。
“我的腿,我的腿,腿,腿……这地,怎生这般溜滑?”
隐隐,有人惊叹:“这,这是第三次了!卢兄,何其霉运?”
楔子三 夫人的哀鸣
安乐坊就在民安坊的东面,两个坊市间就隔着一条人工运河。
和民安坊不同,民安坊住的都是皇亲国戚、开国元勋,而安乐坊里的住户,大半都是后来的国朝新贵。
天恩侯,就是这般的新贵出身。
因为极受天子恩宠的缘故,天恩侯府的规模,甚至比普通的国公府还要大了不少。
同样是占了安乐坊的北面,千多亩大小的府邸建筑极尽壮美。
只是,和民安坊的莱国公府相比,天恩侯府院子里的青松翠柏的树干细了不少。莱国公府院内栽种的各色梅花,千年老梅的树干动辄水缸粗细,而天恩侯府家种的梅花,一颗颗瘦仃仃的就只有胳膊大小。
除了树,天恩侯府的院墙下方,一块块精美的院墙石基上雕刻的花纹也都清晰得很,透着一股子新锐的烟火气。
而莱国公府的院墙,那些石刻的花纹早就密布青苔,风吹雨打过的痕迹,自然带着一份历史积淀的豪门气象。
一大早的,天刚蒙蒙亮,天恩侯府的主妇,侯夫人胡氏就打扮整齐,气喘吁吁的,在两个小丫鬟的搀扶下,有点艰难的爬上了侯府后花园最高的一座楼阁,伸长了脖子朝着西边眺望。
莱国公府在民安坊的位置,和天恩侯府在安乐坊的位置相对,两者之间,隔了一条人工运河,以及大半个民安坊。
就算是天气最好的时候,站在这阁楼上,也看不到莱国公府的动静。
更不要说,如今这漫天飘雪、彤云密布的天光,胡夫人只能看到已经封冻的运河中间,一队队运输物资的雪橇,以及一群群在冰面上打洞钓鱼的顽皮小子。
就连运河对岸的那条密布酒肆饭庄的大街上的动静,以胡夫人的眼力,也是看不清楚的。
只是,胡夫人这些年,就是养成了这毛病。
每天早上,她不到这楼上望一望莱国公府那边的动静,她一整天就连吃饭都没味道。
用手扶了扶头上沉甸甸的金步摇,胡夫人紧了紧身上裹着的火狐狸皮的大氅,有点愁眉苦脸的叹了一口气:“这富贵啊,别人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
两个小丫鬟不敢吭声。
自家夫人惦记着莱国公府那边的家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可是,天恩侯虽然是出自莱国公府,但是如今已经开府别居。虽然是泾阳卢氏的后人,却早已和莱国公府分家了。
除非莱国公府长房直系那一脉的男丁死得干干净净,否则莱国公府那么大的家当,怎么也轮不到天恩侯府惦记的。
那份金山银海一般的家当。
啧啧。
两个小丫鬟盘算着自家夫人往日里的为人,小心翼翼的屏住呼吸,将脑袋深深的低了下去。
“哎,这份富贵啊。”胡夫人咬牙切齿的朝着莱国公府的方向发了一阵狠,用力的跺了跺脚:“叫管家、管事、账房们都过来,这都快小年了,这年底的总账,得好生给我报个清楚了。”
说到‘总账’二字,胡夫人眼睛骤然暴亮。
她语气幽幽的问身边的两个小丫鬟:“你们说,咱家每年年底的账本,就这么几寸厚。”
“听说,他们家每年年底汇总的账本,厚得有五六尺。”
“这么大的家当,他们怎么就消受得起呢?”
两个小丫鬟,越发不敢说话。
半个时辰后,天恩侯府的大厅里,传来了胡夫人恼怒的呵斥声。
“这家绸缎铺,今年的利润比去年少了整整八百二十贯,这钱去哪里了?拖下去,着实、用心、仔细的打,这钱去了哪里,一分不少的给我追回来。”
“这三家粮店,和去年相比,倒也没甚出入。今年的利润,比起去年,倒也差不离。”
“可见你们这三家掌柜,今年是没有用心做事。怎么一点利润都没增加呢?”
“得了,也就不打你们了,可是也别想什么奖励了,滚回去,开年了好生、用心、努力的做事。明年若是还是如此,小心你们的孤拐。”
“嗯,其他的倒也不错。这珠宝店倒是赚了不少,哎,居然比去年多赚了一万八千贯!哎,哎,可不要说夫人我亏待下人,你们都是自家的家生子儿,夫人我最是慷慨、公道、赏罚分明,对你们,可是从来没话说的。”
“你这大掌柜的,你,啧,这年月,钱难赚啊,你,夫人我做主了,赏你二十,不,十贯,回去好生过个肥年。”
“这酒楼……”
“这醋铺……”
“这布庄……”
“这柴店……”
“这牙行……”
“这客栈……”
“这庄子……”
忙碌了大半天,直到傍晚时分,胡夫人终于心满意足的拍了拍手:“好了,安了,妥了,来人啊,把各个铺子缴上来的银钱,好生放入库房。”
“你们可得谨慎小心些,漏了一个铜钱,小心你们的孤拐。”
“今年年景不差,过年的时候,夫人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件新衣服,美不死你们!”
“那布庄的库存里,有十多匹着了雨水的细布,虽然掉了点颜色,那怎么也是精细的好东西,寻常财主都舍不得上身的,能拿来给你们做新衣,整个镐京,除了夫人我,哪里有这么慷慨的主家?你们呀,就偷着乐罢!”
一刻钟后,天恩侯府的后院里,胡夫人如死了亲爹、亲娘的哭喊声冲天而起。
“杀千刀的啊,那个杀千刀的,你怎么又来了?”
“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啊……”
“大前年来了,前年又来!”
“前年来了,去年还来!”
“去年来了,你怎么今年又过来了?”
“你就不能换家人家偷么?”
“盗亦有道,你这是缺德啊,伤天害理啊,薅羊毛逮着咱一家下死手啊!”
“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啊,啊,啊,啊!”
“你们这群没用的废物!”
“吃猪糠长大的赔钱货!”
“活该被千刀万剐的没脑壳的!”
“侯爷让你们看家,你们就是这么看家的么?”
“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啊!”
“呜呜,呜呜,去报官,报官,拿老爷的名扎去报官!”
“多派人去!”
“多派人去!”
“敲鸣冤鼓!”
“叩獬豸钟!”
“抓不到那贼人,谁也别想过一个好年!”
第一章 主母召唤
嘉佑嬉事正文卷第一章主母召唤大胤武朝,嘉佑十八年。
腊月二十,镐京,大雪。
刺骨寒风呼啸着冲进镐京的大街小巷,从路边富贵人家的园子里,卷出了片片梅瓣,混着鹅毛雪片,纷纷扬扬的扫过一片片庭院、屋瓦。
镐京皇城东南,是一品上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大坊的民安坊。
民安坊的东侧,隔着一条宽有数里的人工运河,则是二品上坊安乐坊。
安乐坊,多贵人。
能在安乐坊扎下基业的,多为朱门紫袍的豪门大户。
最近些年,安乐坊中最有名,最奢遮的大人物,莫过于天恩侯卢旲。
占地近千亩,气象恢弘的天恩侯府北面,是侯府后街雨露胡同。
整条后街长近三里,街道南北尽是一座座整整齐齐的院子,居住着泾阳卢氏天恩侯府一脉的各房族人。
雨露胡同最西端,靠着安乐坊一号运河码头,有一处小小的院子。
天寒地冻,运河已经冰封。
天色刚亮,一队队雪橇被膘肥体壮的雪地犬拉拽着,运载着小山一样的柴薪、食盐、米面等日用品,如梭子一般在宽有数里的运河冰面上奔波。
雪橇摩擦冰面的‘嘶嘶’声中,乌黑油亮的长发扎了个单马尾,裹着一件薄薄的青布对襟大棉褂子的卢仚,拉开小院北面正房的房门,深深的吸了一口冰凉刺骨的寒气。
寒气入腹,浑身一片清凉,卢仚刚毅端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和煦的笑容。
慢悠悠走出房门,活动了一下胳膊腿,卢仚抬起头,看了看彤云密布的天空。
“呵,瑞雪兆丰年。”
“嚇,呸,呸,错了,错了。应当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哪!”
扳着手指,卢仚喃喃念叨着。
“嘉佑十五年,谢师宴后,酒后滑倒,折了左小腿。”
“嘉佑十六年,谢师宴后,下楼滚倒,折了右小腿。”
“去年的昨日,依旧是族学年底谢师宴后,如厕摔了个大劈叉,折了左大腿。啧,可是你依旧毫无悔过之心。”
“要不,今年就,三腿齐折?”
卢仚微笑,掐指比划着。
“学聪明了呀,昨天族学散学,你说身体不爽利,将谢师宴改到了今天晚上。”
“避开了昨天,你能避开今天?呵!”
“要不要三腿齐折呢?”
“会不会,太残忍了一些?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也就是故意难为我,连着四年,给我出了四道没法做、不能做、做了就惹祸招灾的道论题嘛!”
“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
“我平日里在族学,在族中,都是平平淡淡,平凡无奇的透明人。”
“你无缘无故的刁难我,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什么仇,什么怨?”
低声念叨中,卢仚走到了小院里的水井旁。
大冬天的,卢仚扒光了身上衣衫,抓起水桶,从水井中打了一桶水,劈头盖脸的泼在了自己身上。
如此连泼了七八桶水,浑身热气升腾的卢仚用手指蘸了点粗盐,狠狠的刷了刷牙齿。
刷牙完毕,身上的水已经被体温蒸发殆尽。
卢仚迎着寒风用力的舒展身体,打了个惬意的呵欠,这才将衣衫重新穿上,大步走到了院子的东边。
在东厢房的角落里,这里种了一小片翠竹,虽然寒冬大雪,这一小片竹子依旧青翠欲滴。
卢仚‘嘶嘶’了几声,在被积雪覆盖的竹叶浓密处,一条拇指粗细,三尺多长的小蛇就轻灵的盘着竹竿游了下来。
这条小蛇通体碧绿,鳞片如宝石一般晶莹剔透,没有一般蛇类的阴森狰狞,反而显得有几分灵性可爱。
如此寒冬,普通蛇类早已冬眠冻僵,这条翠蛇却机灵活泼得很。
翠蛇顺着竹竿滑到了卢仚面前,张开精致的小嘴,‘嘶嘶’吐了吐信子。
卢仚从袖子里掏出了两枚新鲜的鸡蛋,翠蛇前半截身体快若闪电向前一扑,就将两颗鸡蛋生生吞了下去。它摇曳着身体,轻轻的磨蹭着卢仚的手掌,显得格外亲昵。
“去,去,好生歇着。”
卢仚拍了拍翠蛇的脑袋,转身走向了后院。
卢仚的这院子,北边一溜五间正房的后面,有半亩大小的一块土地,平日里种了些常见的蔬菜瓜果,如今已经被雪厚厚的盖了一层。
后院正北面,卢仚挖了个一丈见方的水坑。
大冬天的,这水坑里三尺多深的积水已经冻成了冰块。
一只磨盘大小,通体乌黑的鳄龟懒洋洋的趴在冰上。
听到卢仚的脚步声,鳄龟探出了长脖子,发出了‘咕咕’的叫声,黄豆大小的眼珠乱转,显得格外灵动,甚至很有几分奸猾。
卢仚蹲在水坑旁,掏出了两块新鲜的瘦猪肉。
鳄龟张开大嘴,一口一块,将两块拳头大小的瘦肉吞下,向卢仚轻轻点了点头,又将脑袋、四肢缩回了龟壳里,静静的趴在冰面上。
卢仚伸手,摸了摸鳄龟嶙峋、扎手的背甲,起身走向了院子西侧。
院子的西边,西厢房的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小的窝棚。
一头通体洁白,体型圆胖如球的兔狲正懒洋洋的趴在窝棚里,见到卢仚走了过来,这家伙瞪大蓝幽幽的眼睛,很是不客气的‘哈、哈’吼了两声。
卢仚急忙掏出了两块鸡胸肉,两颗鲜鸡蛋放在了这兔狲的面前。
“大爷,您先吃着,待会不够,您再招呼小的!”
“不打扰您用餐了,您慢慢享用哈!”
卢仚朝着兔狲谄媚一笑,伸手狠狠的在它身上撸了两把,又掏了掏它的下巴,笑呵呵的迈着小碎步,在兔狲不耐烦的‘哈哈’驱赶声中,一溜烟跑向了院子的正南方。
兔狲一爪子按在了一块鸡胸肉上,眼珠朝着卢仚的背影歪了歪,从鼻孔里喷了口冷气。
正南方的杂物房屋檐下,挂着一个通体精钢锻造的大鸟笼。
一支通体火红,不见丝毫杂色,体长能有一尺上下,尾羽长度超过一尺半的大鹦鹉站在鸟笼里,歪着脑袋看着小跑过来的卢仚。
“你妈炸了!”
“你妈炸了!”
“你妈炸得稀碎了!”
大鹦鹉突然开口,扯着嗓子歇斯底里的嚎叫着。
“哎,来了,来了!”
卢仚急忙跑到鸟笼旁,掏出一大把干果仁丢进了鸟笼的食盘里。
大鹦鹉斜着眼瞥了卢仚两眼,浑身羽毛抖了抖,低下头,慢条斯理的啃起了干果。
“你们都是爷!”
卢仚指了指东边的那一丛竹子,指了指北面的水坑、西面的窝棚,伸手进鸟笼,狠狠的捅了捅大鹦鹉肥嘟嘟的肚皮。
“你们一个个,我上辈子欠了你们的?”
“还是大黄憨厚!”
卢仚叹了口气,拍了拍手,走进了杂物房旁的厨房。
一阵响动后,厨房的烟囱里飘出了一道淡淡的烟柱,不多一会儿,就有一股子肉粥的香味在小院子里飘荡。
一条站在地上,头颈几乎有人腰高,从头到尾长近七尺,通体黄毛油光水亮,长的是膘肥体壮精神完足的大黄狗叼着一个硕大的铁盆,慢悠悠的迈着四方步,从正屋中走了出来。
这大黄狗叼着铁盆,慢悠悠的走过小院,静静的蹲在了厨房门口。
一刻钟后。
大黄狗趴在地上,很是从容的舔着铁盆里的肉粥。
它的肉粥里,还窝了几个鸡蛋,肉香、蛋香、米香混在一块,端的香气扑鼻,煞是引人口水。
卢仚端着一个白瓷大海碗,蹲在大黄狗的身边,也不用筷子、汤勺,一小口一小口的喝着肉粥。
‘悉悉索索’,‘悉悉索索’。
那头兔狲吃饱喝足,抖动着浑身肥肉走出了窝棚,绕着小院转起了圈子,一副地主老财巡视自家田土的嘚瑟模样。
大鹦鹉同样吃饱了干果,浑身短毛竖起,将脑袋从鸟笼的栅栏缝隙里挤了出来,朝着那饭后绕圈消食的兔狲挑衅。
“妞,给大爷我笑一个!”
兔狲浑身长毛炸开,犹如一道球形闪电狂奔而来,猛地跳起来几尺高,一爪子扣在了鸟笼上。
就听‘叮叮’几声响,这兔狲的爪子在鸟笼上拉出了几点小火星。
一丛浓密的竹叶中,翠蛇鬼鬼祟祟的探出头来,朝着这边窥视着。
大黄狗吃完了铁盆里的肉粥,抖抖身上长毛,站起身来,朝着鸟笼里的大鹦鹉‘汪汪’吼了几声。
大鹦鹉偃旗息鼓,将脑袋缩回了鸟笼。
大黄狗走到炸毛的兔狲面前,一爪子按在了兔狲的脑袋上。
原本凶神恶煞的兔狲气焰全消,浑身长毛一根根柔顺无比的贴回了身体,‘喵喵’叫着,将脑袋在大黄狗的狗腿上蹭了又蹭。
卢仚也正好喝完了粥,他抓起大黄狗的铁盆,走向了院子角落里的水井,顺路在兔狲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欺软怕硬的狗东西!”
大黄狗瞪大了眼睛,极震惊的看着卢仚,嘴角耷拉了下来,一脸很受伤的小模样。
‘铛铛铛’!
有人重重的敲响了小院的院门,一个难听的公鸭嗓音传了进来:“仚哥儿,仚哥儿?赶紧的,夫人叫你哩。快,快,可不敢让夫人等你!”
已经走到了水井旁,抓着水桶正要丢进井里打水的卢仚呆了呆,放下水桶,抖了抖手上沾着的雪片,一路小步跑到了院门口。
“这一大早的,哪位?”
卢仚拨开门栓,打开院门,一股寒风当面吹来。
一个裹着兔皮大袄子,生得三角眼、三角脸,长相颇为尖酸刻薄的中年男子一把抓住了卢仚的胳膊,拖着他就往外走。
“赶紧的,夫人叫你呢。”
“仚哥儿,我可给你说,夫人这两天火气大着呢,你可别忤逆了她,什么事,都依着顺着哈!”
“要是惹怒了夫人,你这个年,可就难过了!小心你的皮!”
第二章 庸俗的套路
天恩侯府,会客大厅。
陈设华丽的大厅里,天恩侯府主母胡夫人阴沉着脸,端端正正的坐在正中主位上。
见到站在大厅正中的卢仚,身量高挑、丰腴,生得艳若桃李,颇有八九分姿色,只是一双三角眼略显刻薄的胡夫人冷哼了一声,极其挑剔的上下审视着他。
卢仚向胡夫人拱手行礼,恭谨的称呼了一声‘伯母’。
按宗族血脉关系论,卢仚的曾祖父和天恩侯卢旲(tai,通‘大’,‘阳光’)的祖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卢仚是天恩侯正儿八经的同宗侄儿,这一声‘伯母’极是恰当。
大厅中,除了胡夫人,还有两位客人。
一位是身穿青色锦缎长袍,头戴三梁青纱翼冠的男子,看年纪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模样。他坐在胡夫人左手侧的客位上,双手端着细瓷茶盏,翘着二郎腿,一脸傲气,更兼一脸嫌弃的斜眼看着卢仚。
另一位,是一名年龄和卢仚相当,穿着一裘白底墨梅纹大宫裙,上身套着一件银狐皮小马甲,生得唇红齿白、柳眉大眼,身段高挑,楚楚动人如拂风弱柳的少女。
少女本来是清清淡淡,一副红尘万事与己无关的‘世外佳人’模样。
但是猛不丁的见到卢仚,少女的眼睛骤然一亮,目光如火,紧紧的黏在了卢仚端正刚毅、男子气概十足的脸蛋上。
从一对英伟的剑眉,到那一双灿然如寒星明眸,再到那挺拔的鼻梁,有力的唇线,如千炼古铜般淡褐色的皮肤。
少女目光好似涂了胶一样,一寸寸、一丝丝的扫过卢仚的面庞。
随后,她快速的用目光丈量了一番卢仚的身量——她的眸子,又是骤然一亮。
卢仚身高几近九尺,宽肩、狼腰、手腿修长而有力,身形挺拔如一颗青松,加上那刚毅的长相,越发显得阳刚威武,和她平日里交往的那些俊彦气质迥然不同。
但是很快,少女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她微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收敛了表情,又回复了原本清冷清寂,宛如空谷幽兰的气质。
卢仚也禁不住朝少女多看了两眼。
这般颜色的少女,卢仚同样是今生仅见。
他平日里在莱国公府的卢氏族学读书,远远的也见过几次莱国公府的千金小姐们。
那些千金小姐,富贵有余,灵秀不足,气质上,和眼前的少女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只是,这少女美则美矣,却好似画中美人,水中花影,总感觉不够真实。
‘叮当’。
一旁的男子扣上茶盏盖,将茶盏放在了手边小桌几上。
右手在干干净净的长袍衣摆上弹了弹,男子轻声道:“胡夫人,您是侯府主母,天恩侯府上下族人,都归您约束管理,这事,还请您做主。”
面色阴沉的胡夫人挤出了一丝笑容,然后她右手狠狠的在大椅扶手上一拍,用力指了一指卢仚。
“卢仚,可见你是个没福分的破落种子。”
卢仚被胡夫人猛不丁的呵斥声吓了一跳,他愕然看着胡夫人,拱手道:“伯母,小侄哪里做错了?”
胡夫人一脸厌恶的看着他:“丢人现眼的东西。”
微微顿了顿,胡夫人指了指那男子:“这位白邛白大人,你当有印象。”
不等卢仚开口,胡夫人又朝着那少女指了指:“这位白露姑娘,你也当知道她的名字。”
双手用力一拍,胡夫人冷声道:“你配不上人家,所以,交出婚书,再写一份‘自惭才疏学浅,缺德无良’的退婚书给人家,把这事情给了断了罢!”
卢仚瞪大眼,又惊又怒的看了看胡夫人三人,最终目光落在了男子白邛身上。
自认‘才疏学浅’,可以!
自承‘缺德无良’,在大胤武朝,在这个年代,这是要绝人前途,糟践一生!
“是岳父大人当面?”卢仚声音转冷。
白邛的脸色微变,又端起茶盏,用力喝了一大口茶。他不吭一声,连话都懒得和卢仚说一句。
“你还要不要脸?这就叫上岳父了?”胡夫人用力的拍打着扶手,大声的呵斥着:“我天恩侯府卢氏族人中,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寡廉鲜耻,一门心思攀附富贵的混账东西?”
‘寡廉鲜耻、攀附富贵’?
卢仚心头一口恶气直冲了上来,额头正中一条青筋凸起,‘砰砰砰’的急速跳动着。
“伯母,您这话,从何说起?”卢仚的声音也逐渐提高,厉声呵斥道:“我和白家小姐,的确有婚约在身,但是这婚约,却是我祖父留下,那时候,不要说我,就连我父亲都还没有出生,卢仚又如何的‘寡廉鲜耻’,如何的‘攀附富贵’?”
胡夫人语塞。
她虽然是天恩侯府主母,国朝的超品侯夫人。
但是她出身小商人家庭,从小就没读过书的,甚至连字都不认得几个。
在侯府,仗着主母的身份作威作福,她是一等一的好手。
但是要她说道理,要她和人正面驳斥,她就没这能耐了。
白邛冷哼了一声,把玩着手中茶盏盖,依旧不说一句话。
白露轻叹了一口气,双手紧扣放在膝盖上,红唇微动,开口了。
她的声音端的清脆甜美,一如玉珠落入了银盘中,‘叮叮咚咚’的煞是悦耳,就连卢仚心中的火气,也莫名的落下去了几分。
“卢公子所言不虚,你我婚约,的确是两家阿爷当年订下的。”
白露站起身来,俏生生的站在卢仚面前,一双妙眸不离他的俊美面庞。
“一如卢公子所言,当年这婚约签订时,你我父亲都还没有出生,这婚约说到底,只是两位老人家酒后一时兴起罢了。”
白露看着卢仚微笑道:“卢公子以为呢?”
卢仚双手又揣进了袖子里,他目光幽幽的看着白露,冷然道:“酒后一时兴起,这话未免轻佻。想当年,白家阿爷他……”
白露打断了卢仚的话,她笑颜如花的看着卢仚:“毕竟是想当年,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不提当年,只论当下,可好?”
卢仚想要开口,胡夫人已经在一旁呵斥:“闭嘴,听白家小娘怎么说。”
卢仚额头青筋乱跳,用力抿了抿嘴。
天恩侯卢旲,是这一支卢氏族人的家主。
卢旲如今领军镇守在外,天恩侯府,就是胡夫人这个主母当家。
按大胤宗族律法,天恩侯府上下,卢氏数千族人的生死荣辱,尽在胡夫人一念之间。
寻常族人若是被胡夫人发落,真个是被打死了,大胤官府也没有权力插手宗族内务。
卢仚深深吸气,微微低下头,摆出了洗耳恭听的模样。
胡夫人满意的冷笑了一声。
白露浅浅一笑,淡然说道:“当年事情如何,我们也就不说了。但是当今眼下的事情,卢公子还记得,五年前你初次登门,家祖对你说过的话么?”
卢仚当然记得。
五年前,卢仚刚满十岁,按大胤的民俗,十岁少年被称为‘小郎’,即可被视为‘半个成年人’,有资格代表自家出门拜访故旧、结交朋友。
卢仚第一次备了礼物,去白家登门拜会。
那次登门,卢仚没见到白家的其他人,只有白露的祖父白长空出面见了他一面。
在白家,卢仚只喝了半杯半温不火的‘凉’茶,受了白长空几句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殷殷教诲’后,就被‘礼送’离开。
白露见卢仚点头,也微笑颔首:“家祖有言,让你认真读书,努力上进,求一个前程出身,才好履行婚约。”
卢仚的心里一个咯噔。
他抬起头来,认认真真的看了看娇美如花、满脸是笑的白露,又看了看一脸傲气兼不耐烦,翘着二郎腿不断抖动的白邛。
“是,白老先生五年前,让我用功读书,努力上进。他还说,要是我没有读出什么名堂,不仅是自己丢人现眼,更辱没了白家的门风,让白小姐也面上无光。”卢仚的笑容也逐渐灿烂:“所以,这五年来,我再没有登门过。”
白露微笑,目光如火,又在卢仚的俊面上扫了一遍。
白邛在一旁阴阳怪气的说道:“你若是个求上进的,我白家自然乐于和你结了这门亲事。”
摇摇头,白邛将茶盏盖敲击茶盏,敲得‘叮叮’响。
“但是,你看看你这几年,虚耗光阴,荒废了学业,堪称是一事无成,我可没有冤枉你吧?”
用力敲了敲茶盏,白邛数落道:“嘉佑十五年,你族学年底考评,下下。”
“嘉佑十六年,你族学年底考评,下下。”
“嘉佑十七年,你族学年底考评,下下。”
“今年,嘉佑十八年,你族学年底考评,唔,有点进益了,却依旧是下中,依旧是见不得人的成绩!”
白邛摇头长叹道:“我这个人,最是直率,向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来不怕得罪人的。莱国公府的族学,在整个镐京,也不算是好,说三流吧,未免刻薄,若说只是一个二流,却是极恰当的。”
“你在一个二流的族学中,都只能拿到下等考评。”
白邛将茶盏往小桌几上一丢,站起身来,背着双手,走到了卢仚面前,目光森森的盯着卢仚:“你觉得,你有前途么?”
“你觉得,你能名动天下么?”
“你觉得,你能高官显爵么?”
“你觉得,你配得上小女么?”
“你,就不觉得羞惭,不觉得那份婚书,你命弱福薄,担当不起么?”
卢仚额头青筋乱跳。
他想起了这几年他在卢氏族学,每次年底考评,族学学正卢俊给他拟定的道论题目。
用卢俊的话来说,族学是‘量才施教’,所以年底考评,每个人的道论题都是不同的。
但是连续四年,卢俊给卢仚的道论题,都是要人命的啊!
胡夫人在一旁不耐烦的呵斥起来:“好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命!”
“好了,白大人,白小姐,这事情,我做主了。”
“卢仚,交出婚书,再按照我的意思,写一份你主动退婚的契书,这事就这么定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pan.baidu.com/s/13thuXzzvcfPLMSIPbXQ8xQ?pwd=xtia
https://pan.quark.cn/s/7ba03472d48f
为促进文化交流,本站整理收录的小说资源均源自网络公开信息,并遵循以下原则:
1、公益共享:本站为非盈利性文学索引平台,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收费性质的阅读与下载服务;
2、版权归属:所有作品著作权及衍生权利均归属原作者/版权方,本站不主张任何内容所有权;
3、侵权响应:如权利人认为本站展示内容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把该作品相关材料私信至站主或者发件到邮箱。经过核实后,本站将会在48小时内永久下架相关作品。邮箱tegw202@gmail.com
4、用户义务: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利用本站资源进行商业牟利、盗版传播等违法行为。
5、我们始终尊重原创精神,倡导用户通过正版渠道支持创作者。如对版权声明存疑,请联系我们进一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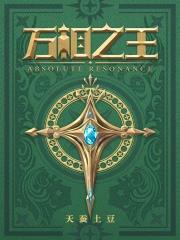


![《[最新]豪乳老师刘艳》连载 (1-9部35章+番外同人) 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uploads/2025/03/20250408195915145-《豪乳老师刘艳》1-8部120章-作者:tttjjj_200-免费小说下载.jpg)















![表情[xiaoku]-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xiaoku.gif) 三十多兆的小说。。。
三十多兆的小说。。。![表情[tuosai]-听风雨阅读](https://tfylion.top/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tuosai.gif)
- 最新
- 最热
查看全部